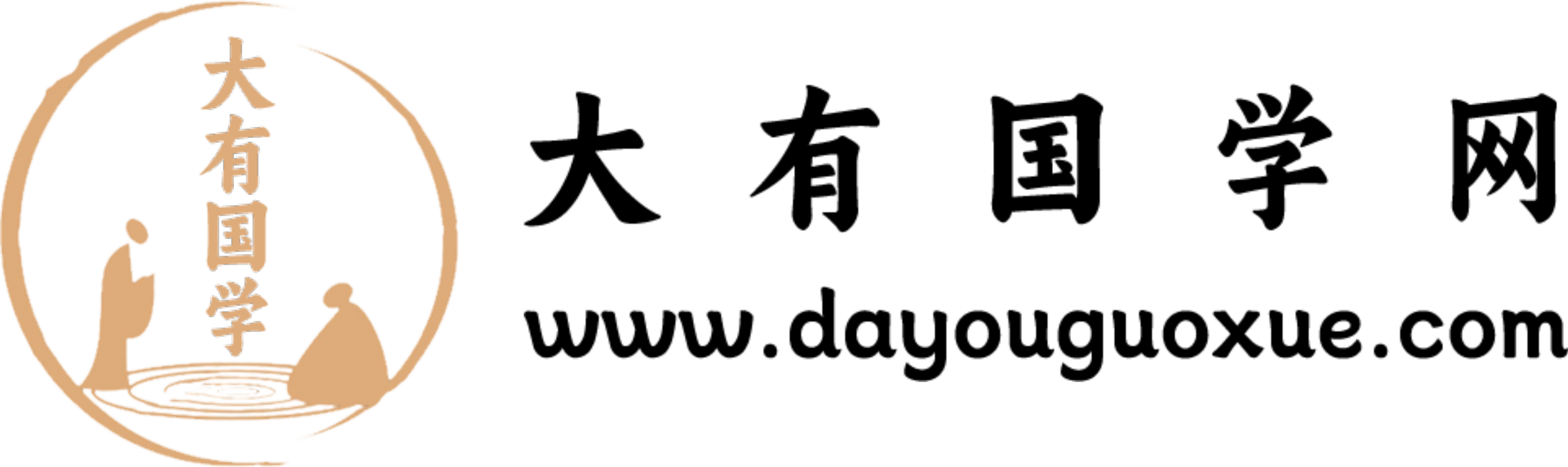范烨 著
原文:
野王二老 向长 逢萌 周党 王霸 严光 井丹 梁鸿 高凤 台佟 韩康 矫慎 戴良 法真 汉阴老父 陈留老父 庞公
《易》称“《遯》之时义大矣哉”。又曰: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。”是以尧称则天,不屈颍阳之高;武尽美矣,终全孤竹之洁。自兹以降,风流弥繁,长往之轨未殊,而感致之数匪一。或隐居以求其志,或回避以全其道,或静已以镇其躁,或去危以图其安,或垢俗以动其概,或疵物以激其清。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,憔悴江海之上,岂必亲鱼鸟、乐林草哉!亦云性分所至而已。故蒙耻之宾,屡黜不去其国;蹈海之节,千乘莫移其情。适使矫易去就,则不能相为矣。彼虽硜硜有类沽名者,然而蝉蜕嚣埃之中,自致寰区之外,异夫饰智巧以逐浮利者乎!荀卿有言曰,“志意修则骄富贵,道义重则轻王公”也。
汉室中微,王莽篡位,士之蕴藉义愤甚矣。是时裂冠毁冕,相携持而去之者,盖不可胜数。杨雄曰:“鸿飞冥冥,弋者何篡焉。”言其违患之远也。光武侧席幽人,求之若不及,旌帛蒲车之所征贲,相望于岩中矣。若薛方、逢萌,聘而不肯至;严光、周党、王霸,至而不能屈。群方咸遂,志士怀仁,斯固所谓“举逸民天下归心”者乎!肃宗亦礼郑均而征高凤,以成其节。自后帝德稍衰,邪{ 薛女}当朝,处子耿介,羞与卿相等列,至乃抗愤而不顾,多失其中行焉。 盖录其绝尘不反,同夫作者,列之此篇。
野王二老者,不知何许人也。初,光武贰于更始,会关中扰乱,遣前将军邓禹西征,送之于道。既反,因于野王猎,路见二老者即禽。光武问曰:“禽何向?”并举手西指,言“此中多虎,臣每即禽,虎亦即臣,大王勿往也。”光武曰:“苟有其备,虎亦何患。”父曰:“何大王之谬邪!昔汤即桀于鸣条,而大城于亳;武王亦即纣于牧野,而大城于郏。彼二王者,其备非不深也。 是以即人者,人亦即之,虽有其备,庸可忽乎!”光武悟其旨,顾左右曰:“此隐者也。”将用之,辞而去,莫知所在。
向长字子平,河内朝歌人也。隐居不仕,性尚中和,好通《老》、《易》。贫无资食,好事者更馈焉,受之取足而反其余。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,连年乃至,欲荐之于莽,固辞乃止。潜隐于家。读《易》至《损》、《益》卦,喟然叹曰:“吾已知富不如贫,贵不如贱,但未知死何如生耳。”建武中,男女娶嫁既毕,敕断家事勿相关,当如我死也。于是遂肆意,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,竟不知所终。
逢萌字子康,北海都昌人也。家贫,给事县为亭长。时尉行过亭,萌候迎拜谒,既而掷CF48叹曰:“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!”遂去之长安学,通《春秋经》。时王莽杀其子宇,萌谓友人曰:“三纲绝矣!不去,祸将及人。”即解冠挂东都城门,归,将家属浮海,客于辽东。
萌素明阴阳,知莽将败,有顷,乃首戴瓦盎,哭于市曰:“新乎新乎!”因遂潜藏。
及光武即位,乃之琅邪劳山,养志修道,人皆化其德。
北海太守素闻其高,遣吏奉谒致礼,萌不答。太守怀恨而使捕之。吏叩头曰:“子康大贤,天下共闻,所在之处,人敬如父,往必不获,只自毁辱。”太守怒,收之系狱,更发它吏。行至劳山,人果相率以兵弩捍御。吏被伤流血,奔而还。后诏书征萌,托以老耄,迷路东西,语使者云:“朝廷所以征我者,以其有益于政,尚不知方面所在,安能济时乎?”即便驾归。连征不起,以寿终。
初,萌与同郡徐房、平原李子云、王君公相友善,并晓阴阳,怀德秽行。房与子云养徒各千人,君公遭乱独不去,侩牛自隐。时人谓之论曰:“避世墙东王君公。”
周党字伯况,太原广武人也。家产千金。少孤,为宗人所养,而遇之不以理,及长,又不还其财。党诣乡县讼,主乃归之。既而散与宗族,悉免遣奴婢,遂至长安游学。
初,乡佐尝众中辱党,党久怀之。后读《春秋》,闻复仇之义,便辍讲而还,与乡佐相闻,期克斗日。既交刃,而党为乡佐所伤,困顿。乡佐服其义,舆归养之,数日方苏,既悟而去。自此敕身修志,州里称其高。
及王莽窃位,托疾杜门。自后贼暴从横,残灭郡县,唯至广武,过城不入。
建武中,征为议郎,以病去职,遂将妻子居黾池。复被征,不得已,乃着短布单衣,穀皮绡头,待见尚书。及光武引见,党伏而不谒,自陈愿守所志,帝乃许焉。
博士范升奏毁党曰:“臣闻尧不须许由、巢父,而建号天下;周不待伯夷、叔齐,而王道以成。伏见太原周党、东海王良、山阳王成等,蒙受厚恩,使者三聘,乃肯就车。及陛见帝廷,党不以礼屈,伏而不谒,偃蹇骄悍,同时俱逝。党等文不能演义,武不能死君,钓采华名,庶几三公之位。臣愿与坐云台之下,考试图国之道。不如臣言,伏虚妄之罪。而敢私窃虚名,夸上求高,皆大不敬。”书奏,天子以示公卿。诏曰:“自古明王圣主,必有不宾之士。伯夷、叔齐不食周粟,太原周党不受朕禄,亦各有志焉。其赐帛四十匹。”党遂隐居黾池,著书上下篇而终。邑人贤而祠之。
初,党与同郡谭贤伯升、雁门殷谟君长,俱守节不仕王莽世。建武中,征,并不到。
王霸字儒仲,太原广武人也。少有清节。及王莽篡位,弃冠带,绝交宦。建武中,征到尚书,拜称名,不称臣。有司问其故。霸曰:“天子有所不臣,诸侯有所不友。”司徒侯霸让位于霸。阎阳毁之曰:“太原俗党,儒仲颇有其风。”遂止。以病归,隐居守志,茅屋蓬户。连征,不至,以寿终。
严光字子陵,一名遵,会稽余姚人也。少有高名,与光武同游学。及光武即位,乃变名姓,隐身不见。帝思其贤,乃令以物色访之。后齐国上言:“有一男子,披羊裘钓泽中。”帝疑其光,乃备安车玄纁,遣使聘之。三反而后至。舍于北军。给床褥,太官朝夕进膳。
司徒侯霸与光素旧,遣使奉书。使人因谓光曰:“公闻先生至,区区欲即诣造。迫于典司,是以不获。愿因日暮,自屈语言。”光不答,乃投札与之,口授曰:“君房足下:位至鼎足,甚善。怀仁辅义天下悦,阿谀顺旨要领绝。”霸得书,封奏之。帝笑曰:“狂奴故态也。”车驾即日幸其馆。光卧不起,帝即其卧所,抚光腹曰:“咄咄子陵,不可相助为理邪?”光又眠不应,良久,乃张目熟视,曰:“昔唐尧著德,巢父洗耳。士故有志,何至相迫乎!”帝曰:“子陵,我竟不能下汝邪?”于是升舆叹息而去。
复引光入,论道旧故,相对累日。帝从容问光曰:“朕何如昔时?”对曰:“陛下差增于往。”因共偃卧,光以足加帝腹上。明日,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。帝笑曰:“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。”
除为谏议大夫,不屈,乃耕于富春山,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。建武十七年,复特征,不至。年八十,终于家。帝伤惜之,诏下郡县赐钱百万、谷千斛。
井丹字大春,扶风郿人也。少受业太学,通《五经》,善谈论,故京师为之语曰:“《五经》纷纶井大春。”性清高,未尝修刺修人。
建武末,沛王辅等五王居北宫,皆好宾客,更遣请丹,不能致。信阳侯阴就,光烈皇后弟也,以外戚贵盛,乃诡说五王,求钱千万,约能致丹,而别使人要劫之。丹不得已,既至,就故为设麦饭葱叶之食。丹推去之,曰:“以君侯能供甘旨,故来相过,何其薄乎?”更置盛馔,乃食。及就起,左右进辇。丹笑曰:“吾闻桀驾人车,岂此邪?”坐中皆失色。就不得已而令去辇。自是隐闭,不关人事,以寿终。
梁鸿字伯鸾,扶风平陵人也。父让,王莽时为城门校尉,封脩远伯,使奉少昊后,寓于北地而卒。鸿时尚幼,以遭乱世,因卷席而葬。
后受业太学,家贫而尚节介,博览无不通,而不为章句。学毕,乃牧豕于上林宛中。曾误遗火,延及它舍。鸿乃寻访烧者,问所去失,悉以豕偿之。其主犹以为少。鸿曰:“无它财,愿以身居作。”主人许之。因为执勤,不懈朝夕。邻家耆老见鸿非恒人,乃共责让主人,而称鸿长者。于是始敬异焉,悉还其豕。鸿不受而去,归乡里。
势家慕其高节,多欲女之,鸿并绝不娶。同县孟氏有女,状肥丑而黑,力举石臼,择对不嫁,至年三十。父母问其故。女曰:“欲得贤如梁伯鸾者。”鸿闻而娉之。女求作布衣、麻屦,织作筐缉绩之具。及嫁,始以装饰入门。七日而鸿不答。妻乃跪床下请曰:“窃闻夫子高义,简斥数妇,妾亦偃蹇数夫矣。今而见择,敢不请罪。”鸿曰:“吾欲裘褐之人,可与俱隐深山者尔。今乃衣绮缟,傅粉墨,岂鸿所愿哉?”妻曰:“以观夫子之志耳。妾自有隐居之服。”乃更为椎髻,着布衣,操作而前。鸿大喜曰:“此真梁鸿妻也。能奉我矣!”字之曰德曜,名孟光。
居有顷,妻曰:“常闻夫子欲隐居避患,今何为默默?无乃欲低头就之乎?”鸿曰:“诺。”乃共入霸陵山中,以耕织为业,咏《诗》、《书》,弹琴以自娱。仰慕前世高士,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。因东出关,过京师,作《五噫之歌》曰:“陟彼北芒兮,噫!顾览帝京兮,噫!宫室崔嵬兮,噫!人之劬劳兮,噫!辽辽未央兮,噫!”肃宗闻而非之,求鸿不得。乃易姓运期,名耀,字侯光,与妻子居齐鲁之间。
有顷,又去适吴。将行,作诗曰:
逝旧帮兮遐征,将遥集兮东南。心惙怛兮伤悴,志菲菲兮升降。欲乘策兮纵迈,疾吾俗兮作谗。竞举枉兮措直,咸先佞兮唌唌。固靡惭兮独建,冀异州兮尚贤。聊逍遥兮遨嬉,缵仲尼兮周流。倘云睹兮我悦,遂舍车兮即浮。过季札兮延陵,求鲁连兮海隅。虽不察兮光貌,幸神灵兮与休。惟季春兮华阜,麦含英兮方秀。哀茂时兮逾迈,愍芳香兮日臭。悼吾心兮不获,长委结兮焉究!口嚣嚣兮余讪,嗟恇恇兮谁留?
遂至吴,依大家皋伯通,居庑下,为人赁舂。每归,妻为具食,不敢于鸿前仰视,举案齐眉。伯通察而异之,曰:“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,非凡人也。”乃方舍之于家。鸿潜闭著书十余篇。疾且困,告主人曰:“昔延陵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间,不归乡里,慎勿令我子持丧归去。”及卒,伯通等为求葬地于吴要离冢傍。咸曰:“要离烈士,而伯鸾清高,可令相近。”葬毕,妻子归扶风。
初,鸿友人京兆高恢,少好《老子》,隐于华阴山中。及鸿东游思恢,作诗曰:“鸟嘤嘤兮友之期,念高子兮仆怀思,相念恢兮EBBC集兹。”二人遂不复相见。恢亦高抗,终身不仕。
高凤字文通,南阳叶人也。少为书生,家以农亩为业,而专精诵读,昼夜不息。妻尝之田,曝麦于庭,令凤护鸡。时天暴雨,而凤持竿诵经,不觉潦水流麦。妻还怪问,凤方悟之。其后遂为名儒,乃教授于西唐山中。
邻里有争财者,持兵而斗,凤往解之,不已,乃脱巾叩头,固请曰:“仁义逊让,奈何弃之!”于是争者怀感,投兵谢罪。
凤年老,执志不倦,名声著闻。太守连召请,恐不得免,自言本巫家,不应为吏,又诈与寡嫂讼田,遂不仕。建初中,将作大匠任隗举凤直言,到公车,托病逃归。推其财产,悉与孤兄子。隐身渔钓,终于家。
论曰:先大夫宣侯,尝以讲道余隙,寓乎逸士之篇。至《高文通传》,辍而有感,以为隐者也,因著其行事而论之曰:“古者隐逸,其风尚矣。颍阳洗耳,耻闻禅让;孤竹长饥,羞食周粟。或高栖以违行,或疾物以矫情,虽轨迹异区,其去就一也。若伊人者,志陵青云之上,身晦泥污之下,心名且犹不显,况怨累之为哉!与夫委体渊沙,鸣弦揆日者,不其远乎!”
台佟字孝威,魏郡鄴人也。隐于武安山,凿穴为居,采药自业。建初中,州辟,不就。刺史行部,乃使从事致谒。佟载病往谢。刺史乃执贽见佟曰:“孝威居身如是,甚苦,如何?”佟曰:“佟幸得保终性命,存神养和。如明使君奉宣诏书,夕惕庶事,反不苦邪?”遂去,隐逸,终不见。
韩康字伯休,一名恬休,京兆霸陵人。家世著姓。常采药名山,卖于长安市,口不二价,三十余年。时有女子从康买药,康守价不移。女子怒曰:“公是韩伯休那?乃不二价乎?”康叹曰:“我本欲避名,今小女子皆知有我,何用药为?”乃遁入霸陵山中。博士公车连征,不至。桓帝乃备玄纁之礼,以安车聘之。使者奉诏造康,康不得已,乃许诺。辞安车,自乘柴车,冒晨先使者发。至亭,亭长以韩征君当过,方发人牛修道桥。及见康柴车幅巾,以为田叟也,使夺其牛。康即释驾与之。有顷,使者至,知夺牛翁乃征君也。使者欲奏杀亭长。康曰:“此自老子与之,亭长何罪!”乃止。康因中道逃遁,以寿终。
矫慎字仲彦,扶风茂陵人也。少好黄、老,隐遁山谷,因穴为室,仰慕松、乔导引之术。与马融、苏章乡里并时,融以才博显名,章以廉直称,然皆推先于慎。
汝南吴苍甚重之,因遗书以观其志曰:
仲彦足下:勤处隐约,虽乘云行泥,栖宿不同,每有西风,何尝不叹!盖闻黄、老之言,乘虚入冥,藏身远遁,亦有理国养人,施于为政。至如登山绝迹,神不著其证,人不睹其验。吾欲先生从其可者,于意何如?昔伊尹不怀道以待尧、舜之君。方今明明,四海开辟,巢、许无为箕山,夷、齐悔入首阳。足下审能骑龙弄凤,翔嬉云间者,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谋也。
慎不答。年七十余,竟不肯娶。后忽归家,自言死日,及期果卒。后人有见慎于敦煌者,故前世异之,或云神仙焉。
慎同郡马瑶,隐于B651山,以兔罝为事。所居俗化,百姓美之,号马牧先生焉。
戴良字叔鸾,汝南慎阳人也。曾祖父遵,字子高,平帝时,为侍御史。王莽篡位,称病归乡里。家富,好给施,尚侠气,食客常三四百人。时人为之语曰:“关东大豪戴子高。”
良少诞节,母憙驴鸣,良常学之,以娱乐焉。及母卒,兄伯鸾居庐啜粥,非礼不行,良独食肉饮酒,哀至乃哭,而二人俱有毁容。或问良曰:“子之居丧,礼乎?”良曰:“然。礼所以制情佚也。情苟不佚,何礼之论!夫食旨不甘,故致毁容之实。若味不存口,食之可也。”论者不能夺之。
良才既高达,而论议尚奇,多骇流俗。同郡谢季孝问曰:“子自视天下孰可为比?”良曰:“我若仲尼长东鲁,大禹出西羌,独步天下,谁与为偶!”
举孝廉,不就。再辟司空府,弥年不到,州郡迫之,乃遁辞诣府,悉将妻子,既行在道,因逃入江夏山中。优游不仕,以寿终。
初,良五女并贤,每有求姻,辄便许嫁,疏裳布被、竹笥木屐以遣之。五女能遵其训,皆有隐者之风焉。
法真字高卿,扶风眉阝人,南郡太守雄之子也。好学而无常家,博通内外图典,为关西大儒。弟子自远方至者,陈留范冉等数百人。性恬静寡欲,不交人间事。太守请见之,真乃幅巾诣谒。太守曰:“昔鲁哀公虽为不肖,而仲尼称臣。太守虚薄,欲以功曹相屈,光赞本朝,何如?”真曰:“以明府见待有礼,故敢自同宾末。若欲吏之,真将在北山之北,南山之南矣。”太守F256然,不敢复言。
辟公府,举贤良,皆不就。同郡田弱荐真曰:“处士法真,体兼四业,学穷典奥,幽居恬泊,乐以忘忧。将蹈老氏之高踪,不为玄纁屈也。臣愿圣朝就加衮职,必能唱《清庙》之歌,致来仪之凤矣。”会顺帝西巡,弱又荐之。帝虚心欲致,前后四征。真曰:“吾既不能遁形远世,岂饮洗耳之水哉?”遂深自隐绝,终不降屈。友人郭正称之曰:“法真名可得闻,身难得而见,逃名而名我随,避名而名我追,可谓百世之师者矣!”乃共刊石颂之,号曰玄德先生。年八十九,中平五年,以寿终。
汉阴老父者,不知何许人也。桓帝延熹中,幸竟陵,过云梦,临沔水,百姓莫不观者,有老父独耕不辍。尚书郎南阳张温异之,使问曰:“人皆来观,老父独不辍,何也?”老父笑而不对。温下道百步,自与言。老父曰:“我野人耳,不达斯语。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?理而立天子邪?立天子以父天下邪?役天下以奉天子邪?昔圣王宰世,茅茨采椽,而万人以宁。今子之君,劳人自纵,逸游无忌。吾为子羞之,子何忍欲人观之乎!”温大惭。问其姓名,不告而去。
陈留老父者,不知何许人也。桓帝世,党锢事起,守外黄令陈留张升去官归乡里,道逢友人,共班草而言。升曰:“吾闻赵杀鸣犊,仲尼临河而反;覆巢竭渊,龙凤逝而不至。今宦竖日乱,陷害忠良,贤人君子其去朝乎?夫德之不建,人之无援,将性命之不免,奈何?”因相抱而泣。老父趋而过之,植其杖,太息言曰:“吁!二大夫何泣之悲也?夫龙不隐鳞,凤不藏羽,网罗高县,去将安所?虽泣何及乎!”二人欲与之语,不顾而去,莫知所终。
庞公者,南郡襄阳人也。居岘山之南,未尝入城府。夫妻相敬如宾。荆州刺史刘表数延请,不能屈,乃就候之。谓曰:“夫保全一身,孰若保全天下乎?”庞公笑曰:“鸿鹄巢于高林之上,暮而得所栖;鼋鼍穴于深渊之下,夕而得所宿。夫趣舍行止,亦人之巢穴也。且各得其栖宿而已,天下非所保也。”因释耕于垄上,而妻子耘于前。表指而问曰:“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,后世何以遗子孙乎?”庞公曰:“世人皆遗之以危,今独遗之以安。虽所遗不同,未为无所遗也。”表叹息而去。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,因采药不反。
赞曰:江海冥灭,山林长往。远性风疏,逸情云上。道就虚全,事违尘枉。
《易》称“《遯》之时义大矣哉”。又曰: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。”是以尧称则天,不屈颍阳之高;武尽美矣,终全孤竹之洁。自兹以降,风流弥繁,长往之轨未殊,而感致之数匪一。或隐居以求其志,或回避以全其道,或静已以镇其躁,或去危以图其安,或垢俗以动其概,或疵物以激其清。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,憔悴江海之上,岂必亲鱼鸟、乐林草哉!亦云性分所至而已。故蒙耻之宾,屡黜不去其国;蹈海之节,千乘莫移其情。适使矫易去就,则不能相为矣。彼虽硜硜有类沽名者,然而蝉蜕嚣埃之中,自致寰区之外,异夫饰智巧以逐浮利者乎!荀卿有言曰,“志意修则骄富贵,道义重则轻王公”也。
汉室中微,王莽篡位,士之蕴藉义愤甚矣。是时裂冠毁冕,相携持而去之者,盖不可胜数。杨雄曰:“鸿飞冥冥,弋者何篡焉。”言其违患之远也。光武侧席幽人,求之若不及,旌帛蒲车之所征贲,相望于岩中矣。若薛方、逢萌,聘而不肯至;严光、周党、王霸,至而不能屈。群方咸遂,志士怀仁,斯固所谓“举逸民天下归心”者乎!肃宗亦礼郑均而征高凤,以成其节。自后帝德稍衰,邪{ 薛女}当朝,处子耿介,羞与卿相等列,至乃抗愤而不顾,多失其中行焉。 盖录其绝尘不反,同夫作者,列之此篇。
野王二老者,不知何许人也。初,光武贰于更始,会关中扰乱,遣前将军邓禹西征,送之于道。既反,因于野王猎,路见二老者即禽。光武问曰:“禽何向?”并举手西指,言“此中多虎,臣每即禽,虎亦即臣,大王勿往也。”光武曰:“苟有其备,虎亦何患。”父曰:“何大王之谬邪!昔汤即桀于鸣条,而大城于亳;武王亦即纣于牧野,而大城于郏。彼二王者,其备非不深也。 是以即人者,人亦即之,虽有其备,庸可忽乎!”光武悟其旨,顾左右曰:“此隐者也。”将用之,辞而去,莫知所在。
向长字子平,河内朝歌人也。隐居不仕,性尚中和,好通《老》、《易》。贫无资食,好事者更馈焉,受之取足而反其余。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,连年乃至,欲荐之于莽,固辞乃止。潜隐于家。读《易》至《损》、《益》卦,喟然叹曰:“吾已知富不如贫,贵不如贱,但未知死何如生耳。”建武中,男女娶嫁既毕,敕断家事勿相关,当如我死也。于是遂肆意,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,竟不知所终。
逢萌字子康,北海都昌人也。家贫,给事县为亭长。时尉行过亭,萌候迎拜谒,既而掷CF48叹曰:“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!”遂去之长安学,通《春秋经》。时王莽杀其子宇,萌谓友人曰:“三纲绝矣!不去,祸将及人。”即解冠挂东都城门,归,将家属浮海,客于辽东。
萌素明阴阳,知莽将败,有顷,乃首戴瓦盎,哭于市曰:“新乎新乎!”因遂潜藏。
及光武即位,乃之琅邪劳山,养志修道,人皆化其德。
北海太守素闻其高,遣吏奉谒致礼,萌不答。太守怀恨而使捕之。吏叩头曰:“子康大贤,天下共闻,所在之处,人敬如父,往必不获,只自毁辱。”太守怒,收之系狱,更发它吏。行至劳山,人果相率以兵弩捍御。吏被伤流血,奔而还。后诏书征萌,托以老耄,迷路东西,语使者云:“朝廷所以征我者,以其有益于政,尚不知方面所在,安能济时乎?”即便驾归。连征不起,以寿终。
初,萌与同郡徐房、平原李子云、王君公相友善,并晓阴阳,怀德秽行。房与子云养徒各千人,君公遭乱独不去,侩牛自隐。时人谓之论曰:“避世墙东王君公。”
周党字伯况,太原广武人也。家产千金。少孤,为宗人所养,而遇之不以理,及长,又不还其财。党诣乡县讼,主乃归之。既而散与宗族,悉免遣奴婢,遂至长安游学。
初,乡佐尝众中辱党,党久怀之。后读《春秋》,闻复仇之义,便辍讲而还,与乡佐相闻,期克斗日。既交刃,而党为乡佐所伤,困顿。乡佐服其义,舆归养之,数日方苏,既悟而去。自此敕身修志,州里称其高。
及王莽窃位,托疾杜门。自后贼暴从横,残灭郡县,唯至广武,过城不入。
建武中,征为议郎,以病去职,遂将妻子居黾池。复被征,不得已,乃着短布单衣,穀皮绡头,待见尚书。及光武引见,党伏而不谒,自陈愿守所志,帝乃许焉。
博士范升奏毁党曰:“臣闻尧不须许由、巢父,而建号天下;周不待伯夷、叔齐,而王道以成。伏见太原周党、东海王良、山阳王成等,蒙受厚恩,使者三聘,乃肯就车。及陛见帝廷,党不以礼屈,伏而不谒,偃蹇骄悍,同时俱逝。党等文不能演义,武不能死君,钓采华名,庶几三公之位。臣愿与坐云台之下,考试图国之道。不如臣言,伏虚妄之罪。而敢私窃虚名,夸上求高,皆大不敬。”书奏,天子以示公卿。诏曰:“自古明王圣主,必有不宾之士。伯夷、叔齐不食周粟,太原周党不受朕禄,亦各有志焉。其赐帛四十匹。”党遂隐居黾池,著书上下篇而终。邑人贤而祠之。
初,党与同郡谭贤伯升、雁门殷谟君长,俱守节不仕王莽世。建武中,征,并不到。
王霸字儒仲,太原广武人也。少有清节。及王莽篡位,弃冠带,绝交宦。建武中,征到尚书,拜称名,不称臣。有司问其故。霸曰:“天子有所不臣,诸侯有所不友。”司徒侯霸让位于霸。阎阳毁之曰:“太原俗党,儒仲颇有其风。”遂止。以病归,隐居守志,茅屋蓬户。连征,不至,以寿终。
严光字子陵,一名遵,会稽余姚人也。少有高名,与光武同游学。及光武即位,乃变名姓,隐身不见。帝思其贤,乃令以物色访之。后齐国上言:“有一男子,披羊裘钓泽中。”帝疑其光,乃备安车玄纁,遣使聘之。三反而后至。舍于北军。给床褥,太官朝夕进膳。
司徒侯霸与光素旧,遣使奉书。使人因谓光曰:“公闻先生至,区区欲即诣造。迫于典司,是以不获。愿因日暮,自屈语言。”光不答,乃投札与之,口授曰:“君房足下:位至鼎足,甚善。怀仁辅义天下悦,阿谀顺旨要领绝。”霸得书,封奏之。帝笑曰:“狂奴故态也。”车驾即日幸其馆。光卧不起,帝即其卧所,抚光腹曰:“咄咄子陵,不可相助为理邪?”光又眠不应,良久,乃张目熟视,曰:“昔唐尧著德,巢父洗耳。士故有志,何至相迫乎!”帝曰:“子陵,我竟不能下汝邪?”于是升舆叹息而去。
复引光入,论道旧故,相对累日。帝从容问光曰:“朕何如昔时?”对曰:“陛下差增于往。”因共偃卧,光以足加帝腹上。明日,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。帝笑曰:“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。”
除为谏议大夫,不屈,乃耕于富春山,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。建武十七年,复特征,不至。年八十,终于家。帝伤惜之,诏下郡县赐钱百万、谷千斛。
井丹字大春,扶风郿人也。少受业太学,通《五经》,善谈论,故京师为之语曰:“《五经》纷纶井大春。”性清高,未尝修刺修人。
建武末,沛王辅等五王居北宫,皆好宾客,更遣请丹,不能致。信阳侯阴就,光烈皇后弟也,以外戚贵盛,乃诡说五王,求钱千万,约能致丹,而别使人要劫之。丹不得已,既至,就故为设麦饭葱叶之食。丹推去之,曰:“以君侯能供甘旨,故来相过,何其薄乎?”更置盛馔,乃食。及就起,左右进辇。丹笑曰:“吾闻桀驾人车,岂此邪?”坐中皆失色。就不得已而令去辇。自是隐闭,不关人事,以寿终。
梁鸿字伯鸾,扶风平陵人也。父让,王莽时为城门校尉,封脩远伯,使奉少昊后,寓于北地而卒。鸿时尚幼,以遭乱世,因卷席而葬。
后受业太学,家贫而尚节介,博览无不通,而不为章句。学毕,乃牧豕于上林宛中。曾误遗火,延及它舍。鸿乃寻访烧者,问所去失,悉以豕偿之。其主犹以为少。鸿曰:“无它财,愿以身居作。”主人许之。因为执勤,不懈朝夕。邻家耆老见鸿非恒人,乃共责让主人,而称鸿长者。于是始敬异焉,悉还其豕。鸿不受而去,归乡里。
势家慕其高节,多欲女之,鸿并绝不娶。同县孟氏有女,状肥丑而黑,力举石臼,择对不嫁,至年三十。父母问其故。女曰:“欲得贤如梁伯鸾者。”鸿闻而娉之。女求作布衣、麻屦,织作筐缉绩之具。及嫁,始以装饰入门。七日而鸿不答。妻乃跪床下请曰:“窃闻夫子高义,简斥数妇,妾亦偃蹇数夫矣。今而见择,敢不请罪。”鸿曰:“吾欲裘褐之人,可与俱隐深山者尔。今乃衣绮缟,傅粉墨,岂鸿所愿哉?”妻曰:“以观夫子之志耳。妾自有隐居之服。”乃更为椎髻,着布衣,操作而前。鸿大喜曰:“此真梁鸿妻也。能奉我矣!”字之曰德曜,名孟光。
居有顷,妻曰:“常闻夫子欲隐居避患,今何为默默?无乃欲低头就之乎?”鸿曰:“诺。”乃共入霸陵山中,以耕织为业,咏《诗》、《书》,弹琴以自娱。仰慕前世高士,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。因东出关,过京师,作《五噫之歌》曰:“陟彼北芒兮,噫!顾览帝京兮,噫!宫室崔嵬兮,噫!人之劬劳兮,噫!辽辽未央兮,噫!”肃宗闻而非之,求鸿不得。乃易姓运期,名耀,字侯光,与妻子居齐鲁之间。
有顷,又去适吴。将行,作诗曰:
逝旧帮兮遐征,将遥集兮东南。心惙怛兮伤悴,志菲菲兮升降。欲乘策兮纵迈,疾吾俗兮作谗。竞举枉兮措直,咸先佞兮唌唌。固靡惭兮独建,冀异州兮尚贤。聊逍遥兮遨嬉,缵仲尼兮周流。倘云睹兮我悦,遂舍车兮即浮。过季札兮延陵,求鲁连兮海隅。虽不察兮光貌,幸神灵兮与休。惟季春兮华阜,麦含英兮方秀。哀茂时兮逾迈,愍芳香兮日臭。悼吾心兮不获,长委结兮焉究!口嚣嚣兮余讪,嗟恇恇兮谁留?
遂至吴,依大家皋伯通,居庑下,为人赁舂。每归,妻为具食,不敢于鸿前仰视,举案齐眉。伯通察而异之,曰:“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,非凡人也。”乃方舍之于家。鸿潜闭著书十余篇。疾且困,告主人曰:“昔延陵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间,不归乡里,慎勿令我子持丧归去。”及卒,伯通等为求葬地于吴要离冢傍。咸曰:“要离烈士,而伯鸾清高,可令相近。”葬毕,妻子归扶风。
初,鸿友人京兆高恢,少好《老子》,隐于华阴山中。及鸿东游思恢,作诗曰:“鸟嘤嘤兮友之期,念高子兮仆怀思,相念恢兮EBBC集兹。”二人遂不复相见。恢亦高抗,终身不仕。
高凤字文通,南阳叶人也。少为书生,家以农亩为业,而专精诵读,昼夜不息。妻尝之田,曝麦于庭,令凤护鸡。时天暴雨,而凤持竿诵经,不觉潦水流麦。妻还怪问,凤方悟之。其后遂为名儒,乃教授于西唐山中。
邻里有争财者,持兵而斗,凤往解之,不已,乃脱巾叩头,固请曰:“仁义逊让,奈何弃之!”于是争者怀感,投兵谢罪。
凤年老,执志不倦,名声著闻。太守连召请,恐不得免,自言本巫家,不应为吏,又诈与寡嫂讼田,遂不仕。建初中,将作大匠任隗举凤直言,到公车,托病逃归。推其财产,悉与孤兄子。隐身渔钓,终于家。
论曰:先大夫宣侯,尝以讲道余隙,寓乎逸士之篇。至《高文通传》,辍而有感,以为隐者也,因著其行事而论之曰:“古者隐逸,其风尚矣。颍阳洗耳,耻闻禅让;孤竹长饥,羞食周粟。或高栖以违行,或疾物以矫情,虽轨迹异区,其去就一也。若伊人者,志陵青云之上,身晦泥污之下,心名且犹不显,况怨累之为哉!与夫委体渊沙,鸣弦揆日者,不其远乎!”
台佟字孝威,魏郡鄴人也。隐于武安山,凿穴为居,采药自业。建初中,州辟,不就。刺史行部,乃使从事致谒。佟载病往谢。刺史乃执贽见佟曰:“孝威居身如是,甚苦,如何?”佟曰:“佟幸得保终性命,存神养和。如明使君奉宣诏书,夕惕庶事,反不苦邪?”遂去,隐逸,终不见。
韩康字伯休,一名恬休,京兆霸陵人。家世著姓。常采药名山,卖于长安市,口不二价,三十余年。时有女子从康买药,康守价不移。女子怒曰:“公是韩伯休那?乃不二价乎?”康叹曰:“我本欲避名,今小女子皆知有我,何用药为?”乃遁入霸陵山中。博士公车连征,不至。桓帝乃备玄纁之礼,以安车聘之。使者奉诏造康,康不得已,乃许诺。辞安车,自乘柴车,冒晨先使者发。至亭,亭长以韩征君当过,方发人牛修道桥。及见康柴车幅巾,以为田叟也,使夺其牛。康即释驾与之。有顷,使者至,知夺牛翁乃征君也。使者欲奏杀亭长。康曰:“此自老子与之,亭长何罪!”乃止。康因中道逃遁,以寿终。
矫慎字仲彦,扶风茂陵人也。少好黄、老,隐遁山谷,因穴为室,仰慕松、乔导引之术。与马融、苏章乡里并时,融以才博显名,章以廉直称,然皆推先于慎。
汝南吴苍甚重之,因遗书以观其志曰:
仲彦足下:勤处隐约,虽乘云行泥,栖宿不同,每有西风,何尝不叹!盖闻黄、老之言,乘虚入冥,藏身远遁,亦有理国养人,施于为政。至如登山绝迹,神不著其证,人不睹其验。吾欲先生从其可者,于意何如?昔伊尹不怀道以待尧、舜之君。方今明明,四海开辟,巢、许无为箕山,夷、齐悔入首阳。足下审能骑龙弄凤,翔嬉云间者,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谋也。
慎不答。年七十余,竟不肯娶。后忽归家,自言死日,及期果卒。后人有见慎于敦煌者,故前世异之,或云神仙焉。
慎同郡马瑶,隐于B651山,以兔罝为事。所居俗化,百姓美之,号马牧先生焉。
戴良字叔鸾,汝南慎阳人也。曾祖父遵,字子高,平帝时,为侍御史。王莽篡位,称病归乡里。家富,好给施,尚侠气,食客常三四百人。时人为之语曰:“关东大豪戴子高。”
良少诞节,母憙驴鸣,良常学之,以娱乐焉。及母卒,兄伯鸾居庐啜粥,非礼不行,良独食肉饮酒,哀至乃哭,而二人俱有毁容。或问良曰:“子之居丧,礼乎?”良曰:“然。礼所以制情佚也。情苟不佚,何礼之论!夫食旨不甘,故致毁容之实。若味不存口,食之可也。”论者不能夺之。
良才既高达,而论议尚奇,多骇流俗。同郡谢季孝问曰:“子自视天下孰可为比?”良曰:“我若仲尼长东鲁,大禹出西羌,独步天下,谁与为偶!”
举孝廉,不就。再辟司空府,弥年不到,州郡迫之,乃遁辞诣府,悉将妻子,既行在道,因逃入江夏山中。优游不仕,以寿终。
初,良五女并贤,每有求姻,辄便许嫁,疏裳布被、竹笥木屐以遣之。五女能遵其训,皆有隐者之风焉。
法真字高卿,扶风眉阝人,南郡太守雄之子也。好学而无常家,博通内外图典,为关西大儒。弟子自远方至者,陈留范冉等数百人。性恬静寡欲,不交人间事。太守请见之,真乃幅巾诣谒。太守曰:“昔鲁哀公虽为不肖,而仲尼称臣。太守虚薄,欲以功曹相屈,光赞本朝,何如?”真曰:“以明府见待有礼,故敢自同宾末。若欲吏之,真将在北山之北,南山之南矣。”太守F256然,不敢复言。
辟公府,举贤良,皆不就。同郡田弱荐真曰:“处士法真,体兼四业,学穷典奥,幽居恬泊,乐以忘忧。将蹈老氏之高踪,不为玄纁屈也。臣愿圣朝就加衮职,必能唱《清庙》之歌,致来仪之凤矣。”会顺帝西巡,弱又荐之。帝虚心欲致,前后四征。真曰:“吾既不能遁形远世,岂饮洗耳之水哉?”遂深自隐绝,终不降屈。友人郭正称之曰:“法真名可得闻,身难得而见,逃名而名我随,避名而名我追,可谓百世之师者矣!”乃共刊石颂之,号曰玄德先生。年八十九,中平五年,以寿终。
汉阴老父者,不知何许人也。桓帝延熹中,幸竟陵,过云梦,临沔水,百姓莫不观者,有老父独耕不辍。尚书郎南阳张温异之,使问曰:“人皆来观,老父独不辍,何也?”老父笑而不对。温下道百步,自与言。老父曰:“我野人耳,不达斯语。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?理而立天子邪?立天子以父天下邪?役天下以奉天子邪?昔圣王宰世,茅茨采椽,而万人以宁。今子之君,劳人自纵,逸游无忌。吾为子羞之,子何忍欲人观之乎!”温大惭。问其姓名,不告而去。
陈留老父者,不知何许人也。桓帝世,党锢事起,守外黄令陈留张升去官归乡里,道逢友人,共班草而言。升曰:“吾闻赵杀鸣犊,仲尼临河而反;覆巢竭渊,龙凤逝而不至。今宦竖日乱,陷害忠良,贤人君子其去朝乎?夫德之不建,人之无援,将性命之不免,奈何?”因相抱而泣。老父趋而过之,植其杖,太息言曰:“吁!二大夫何泣之悲也?夫龙不隐鳞,凤不藏羽,网罗高县,去将安所?虽泣何及乎!”二人欲与之语,不顾而去,莫知所终。
庞公者,南郡襄阳人也。居岘山之南,未尝入城府。夫妻相敬如宾。荆州刺史刘表数延请,不能屈,乃就候之。谓曰:“夫保全一身,孰若保全天下乎?”庞公笑曰:“鸿鹄巢于高林之上,暮而得所栖;鼋鼍穴于深渊之下,夕而得所宿。夫趣舍行止,亦人之巢穴也。且各得其栖宿而已,天下非所保也。”因释耕于垄上,而妻子耘于前。表指而问曰:“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,后世何以遗子孙乎?”庞公曰:“世人皆遗之以危,今独遗之以安。虽所遗不同,未为无所遗也。”表叹息而去。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,因采药不反。
赞曰:江海冥灭,山林长往。远性风疏,逸情云上。道就虚全,事违尘枉。
译文:
野王二老 向长 逢萌 周党 王霸 严光 井丹 梁鸿 高凤 台佟 韩康 矫慎 戴良 法真 汉阴老父 陈留老父 庞公
《易经》讲:“《遁卦》的意思,即隐遁不仕。”《易经》还讲:“不事君王,孤芳自赏。”尧帝以仁政治理天下,颍水以北,依然有巢父、许由隐遁不仕;武王伐纣克殷,拥有天下,可谓尽美,孤竹国君子伯夷、叔齐,坚决不食周粟,以表明其操守。自古以来,就有违逆君王,率性而为的士人。这些社会贤达,特立独行,其风范影响后世。有的隐居在民间,砥砺品行;有的回避权贵,坚守道义;有的修身克己,抚平焦虑;有的视仕途为危途,远离祸殃;有的愤世嫉俗,洁身自律;有的蔑视荣华,清心寡欲。纵观悠游江湖的士人,真的愿意躬耕于垄亩,憔悴于山林,终老于林下,与鱼鸟为伴?抑或说,这本来就是性情使然!柳下惠蒙受尘垢,屡遭贬黜,不肯离开故国;鲁仲连抛弃富贵,蹈海泛舟,不愿改变志向。以矫情处世者,当然不会理解。有些人或许会说,这些士人,不过是沽名钓誉之辈。蝉蜕尘嚣,自鸣于寰宇,与那些凭借智巧,追逐名利者相比,又岂止天壤!荀卿讲:“修身养性,砥砺情操,士人可以傲视富贵;以道义为重,士人可以蔑视王公。”
汉室衰微,王莽篡位,士人心怀义愤,远离朝堂。在当时,撕裂冠盖,毁弃冕旒,挂冠而去者,不计其数。扬雄讲:“鸿鹄高飞,弋猎者何以奈何。”意思是说,士人抛弃官职,远离祸殃,可以全身而退。光武帝即位,虚席以待,以殊礼厚遇士人,求贤若渴,唯恐求之不得,朝廷旌帛蒲车,络绎不绝,来往于招贤的途中。像薛方、逢萌等贤士,依然召而不至,像严光、周党、王霸,即使来到京师,也不肯屈身事君。帝王“举逸民,可令天下归心”,然而天下归心,志士依然可以怀仁,远离权势。章帝即位,以殊礼延请郑均,征召高凤,同时也成全他们的志向。此后,帝德衰微,邪佞掌权,士子耿介,羞与朝廷公卿为伍,有些甚至抗命,已经偏离“中庸之道”的古训。在此辑录愤世嫉俗,隐居民间的士人,编辑《逸民列传》。
野王县有两位老者,不知何许人也。刘秀对更始帝已经怀有二心,正值关中骚乱,刘秀派前将军邓禹西征,在大道上送别。返回时,刘秀顺便在野王县狩猎,路上碰到两位老者追逐野兽。刘秀问:“哪里有野兽?”二人举手,指向西边,说:“此山有老虎,臣每次上山打猎,老虎都会追逐,大王勿往。”刘秀答:“我有准备,老虎又有何惧。”老父说:“大王此话差矣!在往昔,商汤将夏桀流放于鸣条,在亳地建造都城;武王伐纣,在牧野大战,在郏鄏建造城池。二位圣王,准备充分,以武力征伐者,仍然要防备对手反扑,要有所准备,岂可掉以轻心!”刘秀顿时醒悟,对左右人讲:“这二位老父是隐士。”欲起用他们,二人辞别,不知所终。
向长,字子平,河内郡朝歌县人。向长隐居在民间,不肯出仕为官,崇尚中正平和,通晓《易经》、老庄,家中贫困,没有生活来源,有好事者馈送粮食、衣物,向长只留下够吃用的,多余的就归还来者。王莽的大司空王邑,连续几年征召向长,向长来到长安,王邑欲向王莽推荐向长,向长谢绝。此后,向长继续在家中隐居,研究《易经》,读到《损益》篇,向长叹息道:“我知道,富不如贫,贵不如贱,但是,依然不知道死与生,是怎样的关系。”建武年间,向长的子女嫁娶完毕,向长放下家中的事务,犹如已经离世。此后,向长恣意悠游,与好友北海郡人禽庆游历天下五岳名山,不知所终。
逢萌,字子康,北海郡都昌县人。逢萌家中贫困,在县衙当差,后来担任亭长。有一次,县尉路过,逢萌迎候拜谒,过后逢萌将盾牌丢弃在地上,长叹道:“大丈夫岂能供他人役使!”挂冠而去,到长安求学,学习《春秋》。当时,王莽杀了亲生儿子王宇,逢萌对友人讲:“王莽已经抛弃三纲!此时还不走,恐怕会有祸殃。”遂解下衣冠,挂在东都城门上,返回家乡,带上家眷渡过渤海,在辽东郡隐居。
逢萌懂得阴阳转换的道理,知道王莽一定会败亡,不久,逢萌头上顶着瓦盆,在集市上边哭边念:“新莽啊!新莽!”随后隐藏起来。
及至光武帝即位,逢萌在琅琊郡崂山上隐居,修身养性,研习道术,很多人跟随逢萌学习。
北海郡太守听说逢萌高名,多次派官吏拜谒,逢萌避而不见。太守怀恨在心,欲派人逮捕逢萌。被派官吏叩头,说:“子康是一位大贤士,天下人都知道,所到之处,人们犹如敬事父亲。如果逮捕子康,一定难以成功,只能自取其辱。”太守闻言大怒,收捕官吏,关押在监狱,重新派遣官吏。官吏行至崂山,果然,百姓联合起来,手持兵器,官吏被打得头破血流,带伤窜逃回来。后来,朝廷有诏书,征召逢萌。逢萌以年老,辨不清方向为托辞,告诉使者:“朝廷之所以召我,是以为我还能向朝廷提出谏言,对朝政会有所裨益,殊不知,我已经年迈昏聩,连方向都辨认不清,如何辅佐皇上?”逢萌驾车回家。朝廷多次征召,逢萌不肯应召,以寿终。
逢萌与同郡人徐房,平原郡人李子云、王君公的关系很好,几个人都懂得阴阳术,坚持道义,甘守清贫。徐房、李子云教授的学生有上千人,王君公遭逢乱世,不肯出仕为官,在牛市做一个中介,借以隐身。当时人评论:“隐于市井王君公。”
周党,字伯况,太原郡广武县人。周党家产丰厚,有上千金。年少时,周党失去双亲,被族人收养,但是,族人对周党并不好。及至周党长大成人,族人不肯归还周党的家产,周党告到乡里、县里,族人这才归还家产。后来,周党把家产分送予全族人,同时把家里的奴婢遣送回家。而后,周党到长安游学。
最初,乡里的佐吏当众侮辱周党,周党难以释怀。后来,周党读了《春秋》,懂得复仇的道理,之后,周党辍学,返回家乡,与乡里的佐吏约好时间,持刀剑决斗。在决斗中,周党被乡佐刺伤,败下阵来。乡佐佩服周党有勇气,用车子把周党送回家里养伤,经过数日,周党才苏醒,伤愈后,周党离开家乡。从此以后,周党修身励志,州里人称赞周党。
及至王莽篡汉窃位,周党托病,在家乡杜门不出。贼寇肆虐,荼毒地方,但是,贼寇途经广武县,却过城不入。建武年间,朝廷征召周党,拜为议郎,周党以身体有病,辞去官职,带着妻子、儿女迁至渑池县居住。朝廷再次征召,不得已,周党穿着短布衣,系着榖树皮制成的包头巾,来到京师,等候尚书召见。及至尚书向光武帝引见周党,周党伏在地上,不肯拜谒,自述愿意在家乡闭门守志,光武帝答应周党的请求。
博士范升弹劾周党:“臣听说,尧帝没有许由、巢父,照样治理天下;周室没有伯夷、叔齐,照样建立王道。臣看到,太原郡人周党、东海国人王良、山阳国人王成等士人,蒙受朝廷厚恩,使者三番几次征召,才肯应召。及至来到京师,朝见陛下,又不肯按照礼仪,屈身跪拜。周党伏在地上,不肯拜谒,狂妄骄横,竟然与皇上同时退朝。此等士人,文不能推演大义,武不能为国殉难,沽名钓誉,受到朝廷礼遇,几乎与三公一样。臣愿与这些士人,坐在云台下,考试治国之道。如果他们的学问并不像臣所言,臣愿意以虚妄伏罪。如果周党等人自我吹嘘,窃取虚名,应该以不敬治罪。”
奏书递上,天子将奏书展示给朝中公卿,下诏说:“自古以来,明主圣王即位,天下都会有一些不肯臣服的士人。像伯夷、叔齐,宁肯饿死,也不愿意食用周粟。太原郡人周党等,不肯接受朕的俸禄,胸怀志向。赐周党缣帛四十匹。”从此,周党在渑池县隐居,著书上下篇,死在渑池县。当地人称赞周党为贤者,为其建立祠庙。
周党与同郡人谭贤(字伯升)、雁门郡人殷谟(字君长)关系很好,三人都能够坚守节操,不肯在王莽新朝出仕为官。建武年间,朝廷征召,没有应召。
王霸,字儒仲,太原郡广武县人。年轻时,王霸坚守节操,有清名。及至王莽篡位,王霸丢弃冠带,与官员断绝来往。建武年间,朝廷征召王霸,拜为尚书,王霸在觐见皇帝时,只称名,不称臣。有关官员问其原因,王霸答:“天子有所不臣,诸侯有所不友。”司徒(丞相)侯霸欲将丞相位让与王霸。阎阳诋毁王霸:“太原郡的庸俗士人,王儒仲的名气最大。”司徒侯霸这才作罢。王霸以身体有病,辞去官职。在家乡隐居,坚守志向,住在茅草蓬屋。朝廷连续征召,王霸不再应召,以寿终。
严光,字子陵,又名严遵,会稽郡余姚县人。年轻时,严光负有盛名,与刘秀在长安游学。及至刘秀即皇帝位,严光改换姓名,隐身在民间,不再与光武帝见面。光武帝思贤若渴,认为严光是一位贤士,派人按照相貌在民间寻访。后来,齐国上报:“有一位男子,披着羊皮裘衣在湖泽中钓鱼。”光武帝怀疑这就是严光,准备安车、玄 ,派使者前去延请。使者往返三次,礼请严光,严光这才来到京师,暂时住在北军,朝廷供给卧具,太官早晚间送来佳肴。
司徒侯霸与严光有旧交,派使者送来书信,又让使者对严光讲:“丞相听说先生来了,本来要亲自拜访,奈何公务繁忙,不能脱身。等到天晚些时,请先生前去叙谈。”严光听后,没有答话,只是将一副笔札递给使者,口授一封书信,让使者带回去。信中讲:“君房足下:位至鼎足,甚善。怀仁辅义天下悦,阿谀顺旨要杜绝。”侯霸看了书信,密封好,上奏皇帝。光武帝看了,笑着说:“狂奴还是老样子。”当天,光武帝亲临客馆,探视严光。严光躺在床上,不肯起身,光武帝走到床边,摸着严光的肚子:“喂,子陵,不能帮助我治理天下吗?”严光闭着眼睛,不答话。过了一会儿,睁开眼睛,看着光武帝,说:“在往昔,唐尧有圣德,欲禅让天下,巢父听到后,洗耳谢绝。人各有志,何必勉强!”光武帝说:“子陵,我真的不能让你屈就吗?”只好登上乘舆,叹息而归。
后来,光武帝在宫中召见严光,谈起当年在长安求学及过去的老友,相谈甚欢,一连几天,不知疲倦。光武帝从容地问严光:“朕与当年相比,如何?”严光回答:“陛下比当年更见成熟。”二人同床而眠,严光把脚放在皇帝的肚子上。第二天,太史奏报,说有客星侵犯帝座(紫微星座),情况紧急。光武帝笑了,说:“这是朕的老友严子陵,与朕在宫中同床而眠。”
光武帝欲拜严光为谏议大夫,严光不肯屈就,返回富春山,躬耕陇亩,后来,人们把严光垂钓的地方,叫作“严陵濑”。建武十七年,光武帝再次征召严光,严光没有来,在家中去世,享年八十岁。皇帝非常伤心,诏令郡县安排丧事,赐钱一百万、谷一千斛。
井丹,字大春,右扶风郿县人。年轻时,井丹在太学受业,熟读《五经》,善于谈论,京师人为之称道:“五经纷纶井大春。”井丹性情淡泊,为人清高,从来不肯投递名片拜谒官员。
建武末年,沛王刘辅等五位诸侯王居住在北宫,这些诸侯王喜欢结交宾客,多次派人礼请井丹,井丹不肯去。信阳侯阴就是光烈皇后的弟弟,身为外戚,非常尊贵,阴就骗这五位诸侯王,说向井丹求借一千万钱,大约井丹能来,另外再找人半路抢劫。井丹不得已,来见刘辅,阴就特地让厨师准备好麦饭、蔬菜。井丹起身要走,说:“以君侯身份,当然可以准备些佳肴,所以才来相见,为何设宴如此简陋?”重新摆出佳肴,井丹这才坐下来吃饭。及至阴就起身,左右人推出辇车。井丹笑道:“我听说,夏桀用人推车,就是这种车子吗?”座中人闻言大惊。阴就不得已,令人撤回辇车。此后,井丹闭门不出,不与世人交往,以寿终。
梁鸿,字伯鸾,右扶风平陵县人。父亲梁让,在王莽执政时担任长安城门校尉,梁让以少昊帝的后裔,受封为修远伯。(注:王莽以梁让为少昊帝的后裔,封梁让为修远伯。)后来,梁让迁至北地郡,死在北地郡。当时,梁鸿年幼,遭逢乱世,用席子卷着父亲埋葬。
梁鸿在太学接受学业,虽然家中贫困,仍然坚守节操,博览群书,无所不通,不为章句所困。梁鸿完成学业,在上林苑牧猪,有一次用火,误将他人的房子点燃,梁鸿找到房子的主人,问损失多少,愿意将放牧的猪赔偿给对方。房主嫌赔偿太少。梁鸿说:“没有其他财产,愿以自身充当佣工,赔偿损失。”主人答应了。梁鸿在主人家不辞劳苦,早晚间不敢懈怠。邻居家的老人看到梁鸿绝非等闲之辈,责备房屋主人,称梁鸿是一位忠厚长者。主人这才开始尊敬梁鸿,把梁鸿的猪归还给他。梁鸿不肯接受,辞别而去,回到乡里。
有势力的人家敬慕梁鸿品行高尚,多愿意把女儿嫁予梁鸿为妻,梁鸿一概谢绝,不肯聘娶。同县人孟氏有一个女儿,长得肥胖,既丑又黑,力气很大,能举起石臼,但是左挑右选,终不肯出嫁,年龄拖到三十岁。父母问她愿意嫁什么样的人,女儿答:“愿意嫁像梁伯鸾那样的贤士。”梁鸿听说后,遂下聘礼迎娶。为了出嫁,女儿在娘家做了布衣、麻鞋,还有织布用的箩筐及绩麻线用的工具。及至出嫁那一天,女儿才开始梳妆打扮。进门七日,梁鸿不与妻子讲话。妻子跪在地上,默然应对,既而对梁鸿讲:“听说夫子高义,拒绝过几家攀亲的人,妾也曾经拒绝过几家提亲的人。今天已经选择夫子,敢不请罪。”梁鸿答:“我要娶的夫人,是身穿褐色布衣,能与我一起隐居山林的人。如今你身穿丝绸绮缟,脸敷薄粉,岂是梁鸿心目中的妻子?”妻子说:“以此来观察夫子的志向。妾当然有隐居的衣服。”妻子换上布衣,将头发盘起来,梳成椎髻,当着梁鸿的面打扮一番。梁鸿看后大喜,说:“这才是梁鸿的妻子。能与我同甘共苦!”梁鸿为妻子取字“德曜”,名孟光。
二人结婚有一段时间,妻子问:“常听夫子讲,欲隐居山林,躲避祸殃,如今为何默默不语?莫非要俯就官府,屈身任职?”梁鸿答:“你说得对。”于是,二人走入霸陵山,以耕织为业,每天吟咏诗书,以弹琴自娱。梁鸿仰慕前世高士,为西汉商山四皓及此后的二十四位高士作辞颂。
再后来,二人东出函谷关,途经洛阳,梁鸿作《五噫之歌》,歌中道:“登彼北芒兮,噫!远眺帝京兮,噫!宫室崔嵬兮,噫!人之劬劳兮,噫!高高未央兮,噫!”章帝听说后,对歌辞不以为然,访求梁鸿,始终找不到。梁鸿改换姓名,将“梁”改为复姓“运期”,名“耀”,字侯光,与妻子在齐鲁隐居。
过了一段时间,梁鸿又离开齐鲁,准备去吴地。将要出发时,梁鸿作诗道:“逝旧邦兮遐征,将遥集兮东南。心惙怛兮伤悴,志菲菲兮升降。欲乘策兮纵迈,疾吾俗兮作谗。竞举枉兮措直,咸先佞兮唌唌。固靡惭兮独建,冀异州兮尚贤。聊逍遥兮遨嬉,缵仲尼兮周流。傥云睹兮我悦,遂舍车兮即浮。过季札兮延陵,求鲁连兮海隅。虽不察兮光貌,幸神灵兮与休。惟季春兮华阜,麦含含兮方秀。哀茂时兮逾迈,愍芳香兮日臭。悼吾心兮不获,长委结兮焉究!口嚣嚣兮余讪,嗟恇恇兮谁留?”(注:全诗不作翻译)
梁鸿来到吴地,寄居在大户人家皋伯通家,住在廊屋下,为人做佣工,舂米。每天归来,妻子为梁鸿准备好饭食,举案齐眉,不敢仰视。皋伯通看到后,颇为诧异,说:“这个佣工能让妻子如此尊敬,绝非凡俗之人。”
于是,皋伯通重新安排梁鸿,居住在正屋。梁鸿在皋伯通家中潜心著述,撰写了十余篇著作。梁鸿晚年患病,加上贫困,梁鸿告诉主人:“在往昔,延陵季子的儿子死后,埋葬在嬴邑、博邑之间,没有送回家乡安葬,千万告诉我的儿子,别把我送回家乡安葬。”及至去世,皋伯通等人为梁鸿觅得一块墓地,在吴县靠近侠客要离的坟墓旁安葬。大家都说:“要离是一位烈士,伯鸾为人清高,可以比邻而居。”葬礼完毕,妻子回到右扶风。
梁鸿的友人京兆人高恢,年轻时喜欢读《老子》,在华阴县山中隐居。及至梁鸿东游,梁鸿思念高恢,做诗道:“鸟嘤嘤兮友之期,念高子兮仆怀思,想念恢兮爰集兹。”此后,二人没有再相见。高恢也是一位志向高远的士人,终身没有出仕为官。
高凤,字文通,南阳郡叶县人。年轻时,高凤喜欢读书,家中以务农为业,高凤专心向学,昼夜不息。妻子在田间耕作,有一天,在庭院晾晒麦子,让高凤注意看护,不要让鸡啄食。突然天上下暴雨,当时,高凤一手拿着竹竿,一手捧着书籍诵读,不知不觉间,雨水冲走了麦子。妻子回来后责怪高凤,高凤这才省悟。后来,高凤成为一代名儒,在西唐县山中教书授徒。
乡邻有人为财产而争执,甚至手持兵器格斗,高凤前去劝解,没有结果。高凤解下头巾,趴在地上叩头,一再恳求道:“仁义讲究逊让,为何要抛弃仁义!”格斗者受到感动,丢下兵器,相互道歉。
年老后,高凤仍然坚持读书,孜孜不倦,名声传得很远。郡太守多次延请高凤,高凤被纠缠不过,只好说,自己原来是巫师,不应该出来担任官吏,又诈称与寡嫂争田诉讼,太守听后,遂不再勉强。章帝建初年间,将作大匠任隗举荐高凤,说高凤直言敢谏,高凤来到公车署,后又托病,逃回家乡。高凤将家里的财产拿出来,全部送予亡兄的儿子,自己隐居,靠钓鱼为生,在家中去世。
评论如下:先大夫宣侯,曾经在讲学之余,收集整理隐逸士人的事迹。谈到《高文通传》,先大夫对隐士的事迹,颇为感慨。先大夫认为,高文通是一位隐士。《高文通传》里有这样的评语:“在古代,所谓隐逸之士,指的是特立独行的士人,崇尚高风亮节。譬如说许由,在颍水北岸洗耳,耻于听到‘禅让’;譬如说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、叔齐,宁可饿死,也不肯食用周粟。这些隐逸士人,其行为违逆当时的风尚,有些隐逸士人,对物质生活一概排斥,似乎矫情,虽然他们的行为怪异,却都崇尚高风亮节,矢志不移。像高凤这样的士人,怀有青云之志,身陷社会底层,把名气看得犹如浮云,更何况出仕为官,为功名所累!隐逸士人,甘于默默无闻,像屈原,沉沙于汨罗,像嵇康,拂弦高歌唱晚,他们的名气,传得很远!”
台佟,字孝威,魏郡邺县人,在武安县山中隐居,凿穴为室,采药为业。建初年间,州部征召,台佟不肯应召。州部刺史巡行属下县邑,派从事前去拜谒台佟,台佟带病回拜刺史。刺史亲自带着礼物,再次拜谒台佟,说:“孝威先生这样安贫乐道,生活太清苦了,怎么能这样?”台佟答:“台佟幸得以保全性命,修身养性,颐和精神。如果像使君这样,谨奉诏命,四处宣读诏书,朝夕忙碌,夜不能寐,难道就不苦?”台佟离开山中,隐匿起来,不知所终。
韩康,字伯休,又名韩恬休,京兆霸陵县人。韩康的家族是当地大姓。韩康经常在山中采药,到长安集市上售卖,不还二价,有三十余年。有一次,有一个女子从韩康手中买药,韩康不肯还价。女子大怒,说:“公是韩伯休吗?为什么不还二价?”韩康叹道:“我本欲隐姓埋名,今天连一个小女子都知道我,还卖什么药?”遂遁入霸陵县山中。朝中博士乘坐公车前来征召,连续几次,韩康不肯出山。桓帝准备玄纁之礼,派安车聘请韩康,使者奉诏拜谒韩康,韩康不得已,只好答应出山。韩康辞去安车,自己坐着一辆柴车,冒着清晨的霜露,先于使者出发,到了都亭,亭长知道韩征君要从此地经过,正在征调民工、牛车整修道路、桥梁。亭长看到韩康坐着一辆柴车,头戴纶巾,以为是乡间的田舍翁,命人夺去韩康驾车的牛。韩康只好解下驾车的牛,交予亭长。过了一会儿,使者来到,亭长这才知道,刚才的田舍翁就是韩康。使者要杀亭长。韩康说:“这是我主动给他的,亭长无罪!”使者这才没有杀亭长。韩康在途中又逃回家,以寿终。
矫慎,字仲彦,右扶风茂陵县人。年轻时,矫慎喜欢黄老哲学,隐居在山林,凿穴为室,仰慕赤松子、王子乔的导引术,与马融、苏章一样,都是乡里的名人。马融以才学闻名,苏章以正直闻名,然而,二人都很敬重矫慎。
汝南郡人吴苍敬重矫慎,曾经写信给矫慎,以观察其志向,信中讲:“仲彦先生:先生决心隐居山林,世上虽有士人平步青云,也有士人甘守寂寞,志向不同而已。每当西边有先生的消息传来,总会令人唏嘘不已!人们常讲,遵循黄老哲学,甘守寂寞,遁入虚空,藏身于无人知晓之地,仍怀有治国理想,教化百姓,施展抱负。在高山上避开世人,离群索居的贤士,与神仙为侣,难以证明其才学,世人也难以考查其踪迹。我以为,先生应该兼济天下,做这样的贤士,不知意下如何?在往昔,伊尹不以才学疏远尧舜似的圣君。而今,天下太平,政治清明,巢父、许由,应该走下箕山,伯夷、叔齐,应该悔入首阳。先生审时度势,如果能够乘风翔云,展示其才华,这绝非狐兔燕雀之辈可比。”矫慎没有回信,年逾七十,不肯娶妻。有一天,矫慎回到家里,自称死期已到,到了这一天,矫慎去世。后来,有人在敦煌看见矫慎,老一辈人觉得奇怪,有人说矫慎已经成仙。
矫慎同郡人马瑶,在汧山隐居,用罗网捕捉兔子为生。居住的地方,乡风为之改变,百姓称颂马瑶为“马牧先生”。
戴良,字叔鸾,汝南郡慎阳县人。曾祖父戴遵,字子高,在西汉平帝朝担任侍御史。王莽篡位,戴遵称病,返回乡里。戴遵家中富有,愿意施舍财物,崇尚豪侠之气,常有食客三四百。当时人称颂:“关东大侠戴子高。”
戴良从小豪放不羁,母亲喜欢听驴叫,戴良就学驴叫,以娱乐母亲。及至母亲去世,哥哥戴伯鸾另居一室,喝粥度日,非礼不行。戴良却每日饮酒食肉,悲痛时,就放声大哭。二人哀悼母亲,面容憔悴。有人问戴良:“先生这样居丧,合乎礼法吗?”戴良答:“当然符合。礼法,用以抑制感情,如果任由感情恣肆,要礼法又有何用!过分食用美食,美食会损害健康。享用美食,并不过量,又有何不可!”持异议者难以辩驳。
戴良自恃才学甚高,议论新奇,说的话,大多惊世骇俗。同郡人谢季孝问戴良:“先生以为,天下人谁能与先生相比?”戴良答:“我与孔子一样,在东鲁长大,我与大禹一样,走出西羌。我独步天下,谁又能与我相比!”
戴良被举荐为孝廉,不肯就职。两次受到司空府征召,过了一年,仍然不肯到任,州郡强迫,这才搪塞支吾一番,口中说要到郡府走一趟,却带着妻子、儿女,离开家乡,逃入江夏山中。戴良悠游世间,始终不肯出仕为官,以寿终。
最初,戴良有五个女儿,都非常贤淑,有人求婚,戴良也不拒绝,为女儿准备好布被衣裳,以及竹箱、木鞋,送女儿出嫁。五个女儿在婆家,也都能遵循父亲的教诲,颇有其家风。
法真,字高卿,右扶风郿县人,是南郡太守法雄的儿子。法真好学,不拘泥于一家成法,精通内外典籍,被人称为关西大儒。学生从远方来向老师求教,有陈留郡人范冉等数百人。
法真性情恬淡、寡欲,不喜欢参与别人的闲事。郡太守延请法真来见,法真戴着头巾,前去拜谒太守。太守说:“在往昔,鲁哀公虽然不肖,然而仲尼仍然向国君称臣。太守知识浅薄,欲以功曹职务,延请先生屈就,为本朝争光,如何?”法真回答:“明府以礼延请法真,法真才敢以宾客礼陪侍末座。如果明府欲召请法真担任官吏,法真将躲在北山之北,南山之南。”太守目瞪口呆,不敢再言。
朝廷三公府征召法真,举荐法真为贤良,法真谢绝。同郡人田弱举荐法真:“隐士法真,身兼四门学问,饱读诗书,学通经典,隐居在家中避世,生活恬淡自如,甘守清贫,乐以忘忧,愿意追随老子之踪迹,不愿为高官厚禄所迷惑。臣奏请圣朝,可以擢拔任用,法真一定能够辅佐圣朝,颂唱《清庙》之歌,迎接凤凰来仪。”恰逢顺帝西行巡狩,田弱再次举荐法真。顺帝虚心待士,欲将法真召至身边,前后四次。法真说:“我欲避世隐居,岂能饮洗耳之水?”隐藏得更加深绝,始终不肯屈身出仕,降低志向。友人郭正称颂法真:“法真的名字可闻,人却难以见到。法真虽然避世逃名,但是名气很大,隐姓埋名,反而名气尾随而来,可谓百代宗师!”大家共同刊刻碑石,称颂法真,称法真为“玄德先生”。灵帝中平五年,法真以寿终,享年八十九岁。
汉阴县有一位老父,不知何许人也。桓帝延熹年间,桓帝巡幸竟陵,渡过云梦泽,抵达沔水,当地百姓莫不围堵皇帝出巡的仪仗。有一位老父,独自在田间耕作,始终不肯放下手中的农活儿。尚书郎南阳郡人张温看到,很诧异,派人询问老人:“百姓都来看天子出巡,老父却独自在田间耕作,不肯放下手中的农活儿,这是为何?”老父笑而不答。张温走下干道一百步,亲自与老父谈话。老父回答:“我是乡间野人,听不懂你说的话。请问,天下纷乱才有天子?还是天下大治才有天子?天子应该像慈父一样对待生民,还是生民应该像奴婢一样服侍天子?在往昔,圣王治理天下,居住在茅屋,房梁、柱子不加雕饰,天下祥和,万民欢乐。如今的君王,劳苦万民,耽于享乐,四处游幸无度。你们这种人,我只会为之羞愧,你们还好意思让我去围观!”张温听罢,顿感惭愧。问老人姓名,老人不告而别。
陈留郡有一位老父,不知何许人也。在桓帝朝,党锢案骤起,代理外黄县令陈留郡人张升辞官,回到乡里,路上碰到友人,二人坐在草地上谈话。张升说:“我听说,赵简子诛杀鸣犊,孔子走到黄河边,遂折返回去;鸟巢倾覆,深渊枯竭,飞龙、凤凰远逝。如今,宦官祸乱朝纲,陷害忠良,君子是否应该离开朝堂?道德不立,人就会失去精神支柱,我们还要这条老命,有何用?”二人说着,抱头痛哭。有一位老父路过,见此情景,举起手杖,叹息道:“吁!二位大夫为何如此悲泣?飞龙不隐藏鳞甲,凤凰不掩盖羽毛,罗网高悬,何处才是归处?哭泣又有何用!”二人欲与老父交谈,老父不管不顾,扬长而去,不知所终。
庞公,南郡襄阳县人。居住在岘山之南(注:岘山在今湖北省襄阳县东),从未到过城里,夫妻二人相敬如宾。荆州刺史刘表多次延请庞公,庞公不肯屈就,于是刘表亲自来访。刘表问:“保全自身,与保全天下,孰轻孰重?”庞公笑道:“鸿鹄在高大的树枝上筑巢,日暮归来,有栖息之所;鼋鼍在深渊下筑穴,晚夕归来,得以安宿。人的志向,犹如人的巢穴,仅为栖息、安宿而已。保全天下,未必能够保全自身。”庞公将犁铧放置在田垄上,妻子在前边锄地。刘表指着庞公的妻子问:“先生苦于垄亩,不肯出仕为官,能为后世子孙留下什么产业?”庞公答:“世人为后人留下的,都是危险的产业,我留予子孙的,是平安的产业。产业不同罢了,怎么能说没有留下什么?”刘表听罢,叹息而去。后来,庞公带着妻子、儿女登上鹿门山,在山中采药,不再返回乡里。
赞辞如下:江海冥灭,山林长往。远性风疏,逸情云上。道就虚全,事违尘枉。
《易经》讲:“《遁卦》的意思,即隐遁不仕。”《易经》还讲:“不事君王,孤芳自赏。”尧帝以仁政治理天下,颍水以北,依然有巢父、许由隐遁不仕;武王伐纣克殷,拥有天下,可谓尽美,孤竹国君子伯夷、叔齐,坚决不食周粟,以表明其操守。自古以来,就有违逆君王,率性而为的士人。这些社会贤达,特立独行,其风范影响后世。有的隐居在民间,砥砺品行;有的回避权贵,坚守道义;有的修身克己,抚平焦虑;有的视仕途为危途,远离祸殃;有的愤世嫉俗,洁身自律;有的蔑视荣华,清心寡欲。纵观悠游江湖的士人,真的愿意躬耕于垄亩,憔悴于山林,终老于林下,与鱼鸟为伴?抑或说,这本来就是性情使然!柳下惠蒙受尘垢,屡遭贬黜,不肯离开故国;鲁仲连抛弃富贵,蹈海泛舟,不愿改变志向。以矫情处世者,当然不会理解。有些人或许会说,这些士人,不过是沽名钓誉之辈。蝉蜕尘嚣,自鸣于寰宇,与那些凭借智巧,追逐名利者相比,又岂止天壤!荀卿讲:“修身养性,砥砺情操,士人可以傲视富贵;以道义为重,士人可以蔑视王公。”
汉室衰微,王莽篡位,士人心怀义愤,远离朝堂。在当时,撕裂冠盖,毁弃冕旒,挂冠而去者,不计其数。扬雄讲:“鸿鹄高飞,弋猎者何以奈何。”意思是说,士人抛弃官职,远离祸殃,可以全身而退。光武帝即位,虚席以待,以殊礼厚遇士人,求贤若渴,唯恐求之不得,朝廷旌帛蒲车,络绎不绝,来往于招贤的途中。像薛方、逢萌等贤士,依然召而不至,像严光、周党、王霸,即使来到京师,也不肯屈身事君。帝王“举逸民,可令天下归心”,然而天下归心,志士依然可以怀仁,远离权势。章帝即位,以殊礼延请郑均,征召高凤,同时也成全他们的志向。此后,帝德衰微,邪佞掌权,士子耿介,羞与朝廷公卿为伍,有些甚至抗命,已经偏离“中庸之道”的古训。在此辑录愤世嫉俗,隐居民间的士人,编辑《逸民列传》。
野王县有两位老者,不知何许人也。刘秀对更始帝已经怀有二心,正值关中骚乱,刘秀派前将军邓禹西征,在大道上送别。返回时,刘秀顺便在野王县狩猎,路上碰到两位老者追逐野兽。刘秀问:“哪里有野兽?”二人举手,指向西边,说:“此山有老虎,臣每次上山打猎,老虎都会追逐,大王勿往。”刘秀答:“我有准备,老虎又有何惧。”老父说:“大王此话差矣!在往昔,商汤将夏桀流放于鸣条,在亳地建造都城;武王伐纣,在牧野大战,在郏鄏建造城池。二位圣王,准备充分,以武力征伐者,仍然要防备对手反扑,要有所准备,岂可掉以轻心!”刘秀顿时醒悟,对左右人讲:“这二位老父是隐士。”欲起用他们,二人辞别,不知所终。
向长,字子平,河内郡朝歌县人。向长隐居在民间,不肯出仕为官,崇尚中正平和,通晓《易经》、老庄,家中贫困,没有生活来源,有好事者馈送粮食、衣物,向长只留下够吃用的,多余的就归还来者。王莽的大司空王邑,连续几年征召向长,向长来到长安,王邑欲向王莽推荐向长,向长谢绝。此后,向长继续在家中隐居,研究《易经》,读到《损益》篇,向长叹息道:“我知道,富不如贫,贵不如贱,但是,依然不知道死与生,是怎样的关系。”建武年间,向长的子女嫁娶完毕,向长放下家中的事务,犹如已经离世。此后,向长恣意悠游,与好友北海郡人禽庆游历天下五岳名山,不知所终。
逢萌,字子康,北海郡都昌县人。逢萌家中贫困,在县衙当差,后来担任亭长。有一次,县尉路过,逢萌迎候拜谒,过后逢萌将盾牌丢弃在地上,长叹道:“大丈夫岂能供他人役使!”挂冠而去,到长安求学,学习《春秋》。当时,王莽杀了亲生儿子王宇,逢萌对友人讲:“王莽已经抛弃三纲!此时还不走,恐怕会有祸殃。”遂解下衣冠,挂在东都城门上,返回家乡,带上家眷渡过渤海,在辽东郡隐居。
逢萌懂得阴阳转换的道理,知道王莽一定会败亡,不久,逢萌头上顶着瓦盆,在集市上边哭边念:“新莽啊!新莽!”随后隐藏起来。
及至光武帝即位,逢萌在琅琊郡崂山上隐居,修身养性,研习道术,很多人跟随逢萌学习。
北海郡太守听说逢萌高名,多次派官吏拜谒,逢萌避而不见。太守怀恨在心,欲派人逮捕逢萌。被派官吏叩头,说:“子康是一位大贤士,天下人都知道,所到之处,人们犹如敬事父亲。如果逮捕子康,一定难以成功,只能自取其辱。”太守闻言大怒,收捕官吏,关押在监狱,重新派遣官吏。官吏行至崂山,果然,百姓联合起来,手持兵器,官吏被打得头破血流,带伤窜逃回来。后来,朝廷有诏书,征召逢萌。逢萌以年老,辨不清方向为托辞,告诉使者:“朝廷之所以召我,是以为我还能向朝廷提出谏言,对朝政会有所裨益,殊不知,我已经年迈昏聩,连方向都辨认不清,如何辅佐皇上?”逢萌驾车回家。朝廷多次征召,逢萌不肯应召,以寿终。
逢萌与同郡人徐房,平原郡人李子云、王君公的关系很好,几个人都懂得阴阳术,坚持道义,甘守清贫。徐房、李子云教授的学生有上千人,王君公遭逢乱世,不肯出仕为官,在牛市做一个中介,借以隐身。当时人评论:“隐于市井王君公。”
周党,字伯况,太原郡广武县人。周党家产丰厚,有上千金。年少时,周党失去双亲,被族人收养,但是,族人对周党并不好。及至周党长大成人,族人不肯归还周党的家产,周党告到乡里、县里,族人这才归还家产。后来,周党把家产分送予全族人,同时把家里的奴婢遣送回家。而后,周党到长安游学。
最初,乡里的佐吏当众侮辱周党,周党难以释怀。后来,周党读了《春秋》,懂得复仇的道理,之后,周党辍学,返回家乡,与乡里的佐吏约好时间,持刀剑决斗。在决斗中,周党被乡佐刺伤,败下阵来。乡佐佩服周党有勇气,用车子把周党送回家里养伤,经过数日,周党才苏醒,伤愈后,周党离开家乡。从此以后,周党修身励志,州里人称赞周党。
及至王莽篡汉窃位,周党托病,在家乡杜门不出。贼寇肆虐,荼毒地方,但是,贼寇途经广武县,却过城不入。建武年间,朝廷征召周党,拜为议郎,周党以身体有病,辞去官职,带着妻子、儿女迁至渑池县居住。朝廷再次征召,不得已,周党穿着短布衣,系着榖树皮制成的包头巾,来到京师,等候尚书召见。及至尚书向光武帝引见周党,周党伏在地上,不肯拜谒,自述愿意在家乡闭门守志,光武帝答应周党的请求。
博士范升弹劾周党:“臣听说,尧帝没有许由、巢父,照样治理天下;周室没有伯夷、叔齐,照样建立王道。臣看到,太原郡人周党、东海国人王良、山阳国人王成等士人,蒙受朝廷厚恩,使者三番几次征召,才肯应召。及至来到京师,朝见陛下,又不肯按照礼仪,屈身跪拜。周党伏在地上,不肯拜谒,狂妄骄横,竟然与皇上同时退朝。此等士人,文不能推演大义,武不能为国殉难,沽名钓誉,受到朝廷礼遇,几乎与三公一样。臣愿与这些士人,坐在云台下,考试治国之道。如果他们的学问并不像臣所言,臣愿意以虚妄伏罪。如果周党等人自我吹嘘,窃取虚名,应该以不敬治罪。”
奏书递上,天子将奏书展示给朝中公卿,下诏说:“自古以来,明主圣王即位,天下都会有一些不肯臣服的士人。像伯夷、叔齐,宁肯饿死,也不愿意食用周粟。太原郡人周党等,不肯接受朕的俸禄,胸怀志向。赐周党缣帛四十匹。”从此,周党在渑池县隐居,著书上下篇,死在渑池县。当地人称赞周党为贤者,为其建立祠庙。
周党与同郡人谭贤(字伯升)、雁门郡人殷谟(字君长)关系很好,三人都能够坚守节操,不肯在王莽新朝出仕为官。建武年间,朝廷征召,没有应召。
王霸,字儒仲,太原郡广武县人。年轻时,王霸坚守节操,有清名。及至王莽篡位,王霸丢弃冠带,与官员断绝来往。建武年间,朝廷征召王霸,拜为尚书,王霸在觐见皇帝时,只称名,不称臣。有关官员问其原因,王霸答:“天子有所不臣,诸侯有所不友。”司徒(丞相)侯霸欲将丞相位让与王霸。阎阳诋毁王霸:“太原郡的庸俗士人,王儒仲的名气最大。”司徒侯霸这才作罢。王霸以身体有病,辞去官职。在家乡隐居,坚守志向,住在茅草蓬屋。朝廷连续征召,王霸不再应召,以寿终。
严光,字子陵,又名严遵,会稽郡余姚县人。年轻时,严光负有盛名,与刘秀在长安游学。及至刘秀即皇帝位,严光改换姓名,隐身在民间,不再与光武帝见面。光武帝思贤若渴,认为严光是一位贤士,派人按照相貌在民间寻访。后来,齐国上报:“有一位男子,披着羊皮裘衣在湖泽中钓鱼。”光武帝怀疑这就是严光,准备安车、玄 ,派使者前去延请。使者往返三次,礼请严光,严光这才来到京师,暂时住在北军,朝廷供给卧具,太官早晚间送来佳肴。
司徒侯霸与严光有旧交,派使者送来书信,又让使者对严光讲:“丞相听说先生来了,本来要亲自拜访,奈何公务繁忙,不能脱身。等到天晚些时,请先生前去叙谈。”严光听后,没有答话,只是将一副笔札递给使者,口授一封书信,让使者带回去。信中讲:“君房足下:位至鼎足,甚善。怀仁辅义天下悦,阿谀顺旨要杜绝。”侯霸看了书信,密封好,上奏皇帝。光武帝看了,笑着说:“狂奴还是老样子。”当天,光武帝亲临客馆,探视严光。严光躺在床上,不肯起身,光武帝走到床边,摸着严光的肚子:“喂,子陵,不能帮助我治理天下吗?”严光闭着眼睛,不答话。过了一会儿,睁开眼睛,看着光武帝,说:“在往昔,唐尧有圣德,欲禅让天下,巢父听到后,洗耳谢绝。人各有志,何必勉强!”光武帝说:“子陵,我真的不能让你屈就吗?”只好登上乘舆,叹息而归。
后来,光武帝在宫中召见严光,谈起当年在长安求学及过去的老友,相谈甚欢,一连几天,不知疲倦。光武帝从容地问严光:“朕与当年相比,如何?”严光回答:“陛下比当年更见成熟。”二人同床而眠,严光把脚放在皇帝的肚子上。第二天,太史奏报,说有客星侵犯帝座(紫微星座),情况紧急。光武帝笑了,说:“这是朕的老友严子陵,与朕在宫中同床而眠。”
光武帝欲拜严光为谏议大夫,严光不肯屈就,返回富春山,躬耕陇亩,后来,人们把严光垂钓的地方,叫作“严陵濑”。建武十七年,光武帝再次征召严光,严光没有来,在家中去世,享年八十岁。皇帝非常伤心,诏令郡县安排丧事,赐钱一百万、谷一千斛。
井丹,字大春,右扶风郿县人。年轻时,井丹在太学受业,熟读《五经》,善于谈论,京师人为之称道:“五经纷纶井大春。”井丹性情淡泊,为人清高,从来不肯投递名片拜谒官员。
建武末年,沛王刘辅等五位诸侯王居住在北宫,这些诸侯王喜欢结交宾客,多次派人礼请井丹,井丹不肯去。信阳侯阴就是光烈皇后的弟弟,身为外戚,非常尊贵,阴就骗这五位诸侯王,说向井丹求借一千万钱,大约井丹能来,另外再找人半路抢劫。井丹不得已,来见刘辅,阴就特地让厨师准备好麦饭、蔬菜。井丹起身要走,说:“以君侯身份,当然可以准备些佳肴,所以才来相见,为何设宴如此简陋?”重新摆出佳肴,井丹这才坐下来吃饭。及至阴就起身,左右人推出辇车。井丹笑道:“我听说,夏桀用人推车,就是这种车子吗?”座中人闻言大惊。阴就不得已,令人撤回辇车。此后,井丹闭门不出,不与世人交往,以寿终。
梁鸿,字伯鸾,右扶风平陵县人。父亲梁让,在王莽执政时担任长安城门校尉,梁让以少昊帝的后裔,受封为修远伯。(注:王莽以梁让为少昊帝的后裔,封梁让为修远伯。)后来,梁让迁至北地郡,死在北地郡。当时,梁鸿年幼,遭逢乱世,用席子卷着父亲埋葬。
梁鸿在太学接受学业,虽然家中贫困,仍然坚守节操,博览群书,无所不通,不为章句所困。梁鸿完成学业,在上林苑牧猪,有一次用火,误将他人的房子点燃,梁鸿找到房子的主人,问损失多少,愿意将放牧的猪赔偿给对方。房主嫌赔偿太少。梁鸿说:“没有其他财产,愿以自身充当佣工,赔偿损失。”主人答应了。梁鸿在主人家不辞劳苦,早晚间不敢懈怠。邻居家的老人看到梁鸿绝非等闲之辈,责备房屋主人,称梁鸿是一位忠厚长者。主人这才开始尊敬梁鸿,把梁鸿的猪归还给他。梁鸿不肯接受,辞别而去,回到乡里。
有势力的人家敬慕梁鸿品行高尚,多愿意把女儿嫁予梁鸿为妻,梁鸿一概谢绝,不肯聘娶。同县人孟氏有一个女儿,长得肥胖,既丑又黑,力气很大,能举起石臼,但是左挑右选,终不肯出嫁,年龄拖到三十岁。父母问她愿意嫁什么样的人,女儿答:“愿意嫁像梁伯鸾那样的贤士。”梁鸿听说后,遂下聘礼迎娶。为了出嫁,女儿在娘家做了布衣、麻鞋,还有织布用的箩筐及绩麻线用的工具。及至出嫁那一天,女儿才开始梳妆打扮。进门七日,梁鸿不与妻子讲话。妻子跪在地上,默然应对,既而对梁鸿讲:“听说夫子高义,拒绝过几家攀亲的人,妾也曾经拒绝过几家提亲的人。今天已经选择夫子,敢不请罪。”梁鸿答:“我要娶的夫人,是身穿褐色布衣,能与我一起隐居山林的人。如今你身穿丝绸绮缟,脸敷薄粉,岂是梁鸿心目中的妻子?”妻子说:“以此来观察夫子的志向。妾当然有隐居的衣服。”妻子换上布衣,将头发盘起来,梳成椎髻,当着梁鸿的面打扮一番。梁鸿看后大喜,说:“这才是梁鸿的妻子。能与我同甘共苦!”梁鸿为妻子取字“德曜”,名孟光。
二人结婚有一段时间,妻子问:“常听夫子讲,欲隐居山林,躲避祸殃,如今为何默默不语?莫非要俯就官府,屈身任职?”梁鸿答:“你说得对。”于是,二人走入霸陵山,以耕织为业,每天吟咏诗书,以弹琴自娱。梁鸿仰慕前世高士,为西汉商山四皓及此后的二十四位高士作辞颂。
再后来,二人东出函谷关,途经洛阳,梁鸿作《五噫之歌》,歌中道:“登彼北芒兮,噫!远眺帝京兮,噫!宫室崔嵬兮,噫!人之劬劳兮,噫!高高未央兮,噫!”章帝听说后,对歌辞不以为然,访求梁鸿,始终找不到。梁鸿改换姓名,将“梁”改为复姓“运期”,名“耀”,字侯光,与妻子在齐鲁隐居。
过了一段时间,梁鸿又离开齐鲁,准备去吴地。将要出发时,梁鸿作诗道:“逝旧邦兮遐征,将遥集兮东南。心惙怛兮伤悴,志菲菲兮升降。欲乘策兮纵迈,疾吾俗兮作谗。竞举枉兮措直,咸先佞兮唌唌。固靡惭兮独建,冀异州兮尚贤。聊逍遥兮遨嬉,缵仲尼兮周流。傥云睹兮我悦,遂舍车兮即浮。过季札兮延陵,求鲁连兮海隅。虽不察兮光貌,幸神灵兮与休。惟季春兮华阜,麦含含兮方秀。哀茂时兮逾迈,愍芳香兮日臭。悼吾心兮不获,长委结兮焉究!口嚣嚣兮余讪,嗟恇恇兮谁留?”(注:全诗不作翻译)
梁鸿来到吴地,寄居在大户人家皋伯通家,住在廊屋下,为人做佣工,舂米。每天归来,妻子为梁鸿准备好饭食,举案齐眉,不敢仰视。皋伯通看到后,颇为诧异,说:“这个佣工能让妻子如此尊敬,绝非凡俗之人。”
于是,皋伯通重新安排梁鸿,居住在正屋。梁鸿在皋伯通家中潜心著述,撰写了十余篇著作。梁鸿晚年患病,加上贫困,梁鸿告诉主人:“在往昔,延陵季子的儿子死后,埋葬在嬴邑、博邑之间,没有送回家乡安葬,千万告诉我的儿子,别把我送回家乡安葬。”及至去世,皋伯通等人为梁鸿觅得一块墓地,在吴县靠近侠客要离的坟墓旁安葬。大家都说:“要离是一位烈士,伯鸾为人清高,可以比邻而居。”葬礼完毕,妻子回到右扶风。
梁鸿的友人京兆人高恢,年轻时喜欢读《老子》,在华阴县山中隐居。及至梁鸿东游,梁鸿思念高恢,做诗道:“鸟嘤嘤兮友之期,念高子兮仆怀思,想念恢兮爰集兹。”此后,二人没有再相见。高恢也是一位志向高远的士人,终身没有出仕为官。
高凤,字文通,南阳郡叶县人。年轻时,高凤喜欢读书,家中以务农为业,高凤专心向学,昼夜不息。妻子在田间耕作,有一天,在庭院晾晒麦子,让高凤注意看护,不要让鸡啄食。突然天上下暴雨,当时,高凤一手拿着竹竿,一手捧着书籍诵读,不知不觉间,雨水冲走了麦子。妻子回来后责怪高凤,高凤这才省悟。后来,高凤成为一代名儒,在西唐县山中教书授徒。
乡邻有人为财产而争执,甚至手持兵器格斗,高凤前去劝解,没有结果。高凤解下头巾,趴在地上叩头,一再恳求道:“仁义讲究逊让,为何要抛弃仁义!”格斗者受到感动,丢下兵器,相互道歉。
年老后,高凤仍然坚持读书,孜孜不倦,名声传得很远。郡太守多次延请高凤,高凤被纠缠不过,只好说,自己原来是巫师,不应该出来担任官吏,又诈称与寡嫂争田诉讼,太守听后,遂不再勉强。章帝建初年间,将作大匠任隗举荐高凤,说高凤直言敢谏,高凤来到公车署,后又托病,逃回家乡。高凤将家里的财产拿出来,全部送予亡兄的儿子,自己隐居,靠钓鱼为生,在家中去世。
评论如下:先大夫宣侯,曾经在讲学之余,收集整理隐逸士人的事迹。谈到《高文通传》,先大夫对隐士的事迹,颇为感慨。先大夫认为,高文通是一位隐士。《高文通传》里有这样的评语:“在古代,所谓隐逸之士,指的是特立独行的士人,崇尚高风亮节。譬如说许由,在颍水北岸洗耳,耻于听到‘禅让’;譬如说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、叔齐,宁可饿死,也不肯食用周粟。这些隐逸士人,其行为违逆当时的风尚,有些隐逸士人,对物质生活一概排斥,似乎矫情,虽然他们的行为怪异,却都崇尚高风亮节,矢志不移。像高凤这样的士人,怀有青云之志,身陷社会底层,把名气看得犹如浮云,更何况出仕为官,为功名所累!隐逸士人,甘于默默无闻,像屈原,沉沙于汨罗,像嵇康,拂弦高歌唱晚,他们的名气,传得很远!”
台佟,字孝威,魏郡邺县人,在武安县山中隐居,凿穴为室,采药为业。建初年间,州部征召,台佟不肯应召。州部刺史巡行属下县邑,派从事前去拜谒台佟,台佟带病回拜刺史。刺史亲自带着礼物,再次拜谒台佟,说:“孝威先生这样安贫乐道,生活太清苦了,怎么能这样?”台佟答:“台佟幸得以保全性命,修身养性,颐和精神。如果像使君这样,谨奉诏命,四处宣读诏书,朝夕忙碌,夜不能寐,难道就不苦?”台佟离开山中,隐匿起来,不知所终。
韩康,字伯休,又名韩恬休,京兆霸陵县人。韩康的家族是当地大姓。韩康经常在山中采药,到长安集市上售卖,不还二价,有三十余年。有一次,有一个女子从韩康手中买药,韩康不肯还价。女子大怒,说:“公是韩伯休吗?为什么不还二价?”韩康叹道:“我本欲隐姓埋名,今天连一个小女子都知道我,还卖什么药?”遂遁入霸陵县山中。朝中博士乘坐公车前来征召,连续几次,韩康不肯出山。桓帝准备玄纁之礼,派安车聘请韩康,使者奉诏拜谒韩康,韩康不得已,只好答应出山。韩康辞去安车,自己坐着一辆柴车,冒着清晨的霜露,先于使者出发,到了都亭,亭长知道韩征君要从此地经过,正在征调民工、牛车整修道路、桥梁。亭长看到韩康坐着一辆柴车,头戴纶巾,以为是乡间的田舍翁,命人夺去韩康驾车的牛。韩康只好解下驾车的牛,交予亭长。过了一会儿,使者来到,亭长这才知道,刚才的田舍翁就是韩康。使者要杀亭长。韩康说:“这是我主动给他的,亭长无罪!”使者这才没有杀亭长。韩康在途中又逃回家,以寿终。
矫慎,字仲彦,右扶风茂陵县人。年轻时,矫慎喜欢黄老哲学,隐居在山林,凿穴为室,仰慕赤松子、王子乔的导引术,与马融、苏章一样,都是乡里的名人。马融以才学闻名,苏章以正直闻名,然而,二人都很敬重矫慎。
汝南郡人吴苍敬重矫慎,曾经写信给矫慎,以观察其志向,信中讲:“仲彦先生:先生决心隐居山林,世上虽有士人平步青云,也有士人甘守寂寞,志向不同而已。每当西边有先生的消息传来,总会令人唏嘘不已!人们常讲,遵循黄老哲学,甘守寂寞,遁入虚空,藏身于无人知晓之地,仍怀有治国理想,教化百姓,施展抱负。在高山上避开世人,离群索居的贤士,与神仙为侣,难以证明其才学,世人也难以考查其踪迹。我以为,先生应该兼济天下,做这样的贤士,不知意下如何?在往昔,伊尹不以才学疏远尧舜似的圣君。而今,天下太平,政治清明,巢父、许由,应该走下箕山,伯夷、叔齐,应该悔入首阳。先生审时度势,如果能够乘风翔云,展示其才华,这绝非狐兔燕雀之辈可比。”矫慎没有回信,年逾七十,不肯娶妻。有一天,矫慎回到家里,自称死期已到,到了这一天,矫慎去世。后来,有人在敦煌看见矫慎,老一辈人觉得奇怪,有人说矫慎已经成仙。
矫慎同郡人马瑶,在汧山隐居,用罗网捕捉兔子为生。居住的地方,乡风为之改变,百姓称颂马瑶为“马牧先生”。
戴良,字叔鸾,汝南郡慎阳县人。曾祖父戴遵,字子高,在西汉平帝朝担任侍御史。王莽篡位,戴遵称病,返回乡里。戴遵家中富有,愿意施舍财物,崇尚豪侠之气,常有食客三四百。当时人称颂:“关东大侠戴子高。”
戴良从小豪放不羁,母亲喜欢听驴叫,戴良就学驴叫,以娱乐母亲。及至母亲去世,哥哥戴伯鸾另居一室,喝粥度日,非礼不行。戴良却每日饮酒食肉,悲痛时,就放声大哭。二人哀悼母亲,面容憔悴。有人问戴良:“先生这样居丧,合乎礼法吗?”戴良答:“当然符合。礼法,用以抑制感情,如果任由感情恣肆,要礼法又有何用!过分食用美食,美食会损害健康。享用美食,并不过量,又有何不可!”持异议者难以辩驳。
戴良自恃才学甚高,议论新奇,说的话,大多惊世骇俗。同郡人谢季孝问戴良:“先生以为,天下人谁能与先生相比?”戴良答:“我与孔子一样,在东鲁长大,我与大禹一样,走出西羌。我独步天下,谁又能与我相比!”
戴良被举荐为孝廉,不肯就职。两次受到司空府征召,过了一年,仍然不肯到任,州郡强迫,这才搪塞支吾一番,口中说要到郡府走一趟,却带着妻子、儿女,离开家乡,逃入江夏山中。戴良悠游世间,始终不肯出仕为官,以寿终。
最初,戴良有五个女儿,都非常贤淑,有人求婚,戴良也不拒绝,为女儿准备好布被衣裳,以及竹箱、木鞋,送女儿出嫁。五个女儿在婆家,也都能遵循父亲的教诲,颇有其家风。
法真,字高卿,右扶风郿县人,是南郡太守法雄的儿子。法真好学,不拘泥于一家成法,精通内外典籍,被人称为关西大儒。学生从远方来向老师求教,有陈留郡人范冉等数百人。
法真性情恬淡、寡欲,不喜欢参与别人的闲事。郡太守延请法真来见,法真戴着头巾,前去拜谒太守。太守说:“在往昔,鲁哀公虽然不肖,然而仲尼仍然向国君称臣。太守知识浅薄,欲以功曹职务,延请先生屈就,为本朝争光,如何?”法真回答:“明府以礼延请法真,法真才敢以宾客礼陪侍末座。如果明府欲召请法真担任官吏,法真将躲在北山之北,南山之南。”太守目瞪口呆,不敢再言。
朝廷三公府征召法真,举荐法真为贤良,法真谢绝。同郡人田弱举荐法真:“隐士法真,身兼四门学问,饱读诗书,学通经典,隐居在家中避世,生活恬淡自如,甘守清贫,乐以忘忧,愿意追随老子之踪迹,不愿为高官厚禄所迷惑。臣奏请圣朝,可以擢拔任用,法真一定能够辅佐圣朝,颂唱《清庙》之歌,迎接凤凰来仪。”恰逢顺帝西行巡狩,田弱再次举荐法真。顺帝虚心待士,欲将法真召至身边,前后四次。法真说:“我欲避世隐居,岂能饮洗耳之水?”隐藏得更加深绝,始终不肯屈身出仕,降低志向。友人郭正称颂法真:“法真的名字可闻,人却难以见到。法真虽然避世逃名,但是名气很大,隐姓埋名,反而名气尾随而来,可谓百代宗师!”大家共同刊刻碑石,称颂法真,称法真为“玄德先生”。灵帝中平五年,法真以寿终,享年八十九岁。
汉阴县有一位老父,不知何许人也。桓帝延熹年间,桓帝巡幸竟陵,渡过云梦泽,抵达沔水,当地百姓莫不围堵皇帝出巡的仪仗。有一位老父,独自在田间耕作,始终不肯放下手中的农活儿。尚书郎南阳郡人张温看到,很诧异,派人询问老人:“百姓都来看天子出巡,老父却独自在田间耕作,不肯放下手中的农活儿,这是为何?”老父笑而不答。张温走下干道一百步,亲自与老父谈话。老父回答:“我是乡间野人,听不懂你说的话。请问,天下纷乱才有天子?还是天下大治才有天子?天子应该像慈父一样对待生民,还是生民应该像奴婢一样服侍天子?在往昔,圣王治理天下,居住在茅屋,房梁、柱子不加雕饰,天下祥和,万民欢乐。如今的君王,劳苦万民,耽于享乐,四处游幸无度。你们这种人,我只会为之羞愧,你们还好意思让我去围观!”张温听罢,顿感惭愧。问老人姓名,老人不告而别。
陈留郡有一位老父,不知何许人也。在桓帝朝,党锢案骤起,代理外黄县令陈留郡人张升辞官,回到乡里,路上碰到友人,二人坐在草地上谈话。张升说:“我听说,赵简子诛杀鸣犊,孔子走到黄河边,遂折返回去;鸟巢倾覆,深渊枯竭,飞龙、凤凰远逝。如今,宦官祸乱朝纲,陷害忠良,君子是否应该离开朝堂?道德不立,人就会失去精神支柱,我们还要这条老命,有何用?”二人说着,抱头痛哭。有一位老父路过,见此情景,举起手杖,叹息道:“吁!二位大夫为何如此悲泣?飞龙不隐藏鳞甲,凤凰不掩盖羽毛,罗网高悬,何处才是归处?哭泣又有何用!”二人欲与老父交谈,老父不管不顾,扬长而去,不知所终。
庞公,南郡襄阳县人。居住在岘山之南(注:岘山在今湖北省襄阳县东),从未到过城里,夫妻二人相敬如宾。荆州刺史刘表多次延请庞公,庞公不肯屈就,于是刘表亲自来访。刘表问:“保全自身,与保全天下,孰轻孰重?”庞公笑道:“鸿鹄在高大的树枝上筑巢,日暮归来,有栖息之所;鼋鼍在深渊下筑穴,晚夕归来,得以安宿。人的志向,犹如人的巢穴,仅为栖息、安宿而已。保全天下,未必能够保全自身。”庞公将犁铧放置在田垄上,妻子在前边锄地。刘表指着庞公的妻子问:“先生苦于垄亩,不肯出仕为官,能为后世子孙留下什么产业?”庞公答:“世人为后人留下的,都是危险的产业,我留予子孙的,是平安的产业。产业不同罢了,怎么能说没有留下什么?”刘表听罢,叹息而去。后来,庞公带着妻子、儿女登上鹿门山,在山中采药,不再返回乡里。
赞辞如下:江海冥灭,山林长往。远性风疏,逸情云上。道就虚全,事违尘枉。